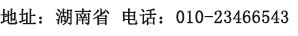我跟着老皮四处偷窃,因为触动了刑警队高层的利益而被抓走,甚至被严刑逼供。以往警察高大的形象逐渐在我心中崩塌,没有任何背景的我只能听天由命,就算是被当成了踏板也一无所知……
3
0
7
我跪在地上,
背铐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
跪了也最少三个小时了,
头上的汗比五月里在麦田里割麦还澎湃。
我的头几乎垂到地上,
试图卸载背铐带来的巨大痛楚。
张玉奎坐在凳子上,
用皮鞋尖勾住我的下巴说:
“你不说也行,
只要你说了那个老皮的事儿,
就算立功了。”
1
我被抓那天,距离十八岁的生日还有三天。
那晚,我正和老皮以及他的女友在他潮湿的地下室吃火锅。
老皮瘸了一条腿,那次他为了盗窃一捆电缆,被冀中四矿的保安追得从三楼跳下。据他说,他的小腿骨都穿破皮肤扎了出来,就这样,他还是一瘸一拐地跑了。
道上的人都很敬佩他,尊称他为“皮哥”。
老皮说他比我大三岁,但是看他满脸的沧桑,估计比我大十岁都不止。
老皮眼前的这个女朋友,叫彭玉花,邢台人,身材特别好,胸脯特别大,很喜欢穿着一些紧身的衣服,害得老皮刚遇见她的那几天,根本就没下过床。
关于老皮和彭玉花的相遇也很有戏剧性,那是十几大前夕,作为老皮的搭档,我们隔三差五被当地的警察例行传唤,就在那天,我们俩刚从派出所出来往外走,在门口遇见了正被两个警察押着进来的彭玉花。
彭玉花丰满的胸脯差点顶到个子矮小的老皮的脸上。
老皮吓了一跳,急忙跳开,惹得几个女警哈哈大笑起来。
出了派出所的大门,老皮伸手掏烟,却掏出一根金条。
老皮的脸色陡然变了,他很聪明,知道这根金条的来历,于是就在派出所门口一直等到天黑彭玉花出来。
彭玉花倒是很吃惊:“你小子怎么没有跑?还等着还我?”
老皮一本正经地说:“盗亦有道,我不能趁人之危。”
就这样,彭玉花这个女扒手和贼头老皮开始拍拖。
2
偷,按照彭玉花说的,也有行话:像我和老皮这样专偷厂矿的叫“吃公食”,偷摩托车的叫“踢飞子”,她属于“抠皮子”,就是警察们口中说的扒手。
彭玉花比老皮小一岁,但是她已经走遍了大江南北,社会阅历极为丰富。但是她说,这老皮是她遇见的最仗义的一个。
老皮答应和她结婚,当着我的面就把彭玉花抱到了床上,一边亲吻一边说:“这两天去领证!”
看着失去理智的老皮和白花花的彭玉花,我急忙捂着眼往外跑,慌乱中还触翻了桌子,火锅倒扣在地上,汤汁顺着地板砖四下里流淌,一股土豆、鱼丸、劣质羊肉的骚味,在十几平米的逼仄地下室蔓延开来。
见我要跑,老皮吼了一声:“二子,去外面等我,一会儿去化肥厂的旧操场。”
老皮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还趴在彭玉花的身上,以至于他这句话都是有规律地两个字两个字地艰难地往外蹦。
随着化肥厂搬迁,化肥厂的旧操场早已经废弃,那里埋着我们俩的一个梦,埋着我们俩的前途。
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和老皮偷了附近的一个化工厂。
那个化工厂在我们镇的上游,排出来的污水顺着村北的泉水川一直流到下游的村庄,好几个村子的人们联合告状,也没能扳倒那个化工厂。
老皮的父亲据说是这场事件中的始作俑者,还被县里刑警队的干警们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带走过。
老皮的父亲回来后,在床上躺了两天,再也没有去化工厂闹腾过,有人再来撺掇去告化工厂的时候,他也只是劝诫那些人。因为那个化工厂有人撑腰,那个人就是刑警队长——张玉奎。
在老皮父亲躺倒第三天的时候,老皮来找我,说去化工厂走一趟。
老皮不知从哪弄来一身化工厂里天蓝色的粗布工作服,他穿上工作服,戴上口罩,大摇大摆就混了进去,我紧张得要命,扛着个铁锹像是跟班的小工一样为他掩护。
他在化工厂转了一圈,晚上就带着我进了财务室,财务室AA88的锁子在白天就被他找机会换了。他依然穿着那件工作服,而且还让我推了一辆手推车,直接就去财务室把那个保险柜抬下来拉走了。
3
我们俩把这保险柜拉到废弃的化肥厂操场上,鼓捣了一晚上也没有打开,没办法,就直接把它埋在了操场下,等有空了,我们再来研究打开。
为了祝贺这次的胜利,老皮问我想要什么犒赏。
我犹豫了一下说:“狐狸街的洗头房究竟理发不?”
老皮呵呵笑了。
第二天,一个巨大的新闻传遍了我们的小镇,那个化工厂丢失了15万巨款,是用来购买新设备的款项,当时几十个警察拉起了警戒线,把整个化工厂都围了起来。
有人指着一个身材矮小、摘下帽子之后稀稀落落几根黄发耷拉在额头的干警小声说:“看,刑警队长张玉奎也来了。”
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绰号“稀毛玉奎”。
他父亲是县里公安局的代局长兼政委。
15万,一个巨大的数额,我们曾经对照一些盗窃数额和刑罚的尺度得出,要是案发,我们最少都得十年以上。
那埋葬的保险柜是我们的禁区,我们再也没有提过。
现在,老皮竟然说出,我们要挖出那个关系着我们命运的保险柜,他说要用里面的钱为彭玉花办一场体面的婚礼。
他不知道,做贼的不能动情,因为山野万里,情是隐藏在罪恶之下的红颜杀手。
我在门口,还能听见老皮的那张陈旧的床不堪重负,吱吱呀呀地摇落他的口无遮拦。
须臾,彭玉花扶着墙走出来,她头发凌乱,裙摆折皱,脸上的红晕还未散去,汗涔涔的。她看了我一眼,故意把胸脯用力挺了一下,我赶紧低下头去。
她却用力摩挲了我的头,叹了口气,离开了。
过了十几分钟,老皮一边系皮带,一边趿拉着鞋子走出来问:“你嫂子去哪儿了?”
我说:“不知道,可能是去买避孕药了。”
老皮看了我一眼,继而笑了说:“你这个小屁孩知道啥,我们从不用那玩意儿,太贵了。”
老皮拿上铁锹带着我去挖那个保险柜。
4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十点钟的光景,世界像是死了一般安静,月亮被冻得也几乎凝固了。
我们一边挖,老皮一边憧憬:“二子,这里面真的有十几万的话,我们一人一半,以后谁也不许再做这营生了。”
我幻想着,这么多钱怎么花。我父母去世得早,不然我也不会跟老皮这个被人们称作人渣的人混在一起。
保险柜埋得并不深,所以十几分钟后,在清冷的月光下,那个蓝色釉质的柜子露了出来。
我和老皮弯下腰,正要合力拽出来,忽然就听见周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们提着的心一揪,知道出事了。
我和老皮还没有转身,就被一伙人扑倒在地狠狠摁住了。我的脸被人踩着,陷进刚挖出来的磕磕绊绊的冰冷泥土里,双手被扯到背后,戴上了手铐。
当我被重新拉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稀毛张玉奎。
我和老皮被他们塞进警车里,那是我们噩梦的开始。
我们被他们拳打脚踢,头扎在车底,脖子几乎窝断。
我心想:不是说警察叔叔不打人吗?小时候,电视上看到的警察叔叔高大上的形象完全被这几个人颠覆了。
警车七拐八拐地进了县公安局。
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审讯室,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死去活来,什么叫生不如死。
张玉奎几乎用遍了所有酷刑:胶皮棍、电棍、摇电话、背铐、熬鹰。
这些刑罚他都能玩出花来,在用电棍点我的时候,他让人掰开我的嘴,将电棍狠狠插进我的嘴里,直到喉咙,以至于后来几天我的舌头都是黑色的。
摇电话,就是把之前淘汰下来的老式电话机的线接到两个大拇指上,然后开始摇,在电流接通的一刹那,心脏似乎都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一股皮肉烧焦的味道从拇指上传了过来……
背铐很厉害,用的铐子是特质的指铐,只铐住人的两个大拇指,左手从后背反着向右肩胛抻展,右手从右肩反着够着左拇指,然后将两个拇指铐住。
据说,曾经有人上背铐四个小时,胳膊废了。
相比这些,更厉害的是熬鹰。
5
不过我没有尝到。
之所以对我使用这闻所未闻的刑罚,是为了从我嘴里套取出更大更多的犯罪事实。
可是,除了盗窃保险柜之外,我和老皮总共就做过六次其他的,而且每次都是小打小闹的,金额不过百元左右。
但是,张玉奎不信,为了从我嘴里拷问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来,就只有一个办法,逼供。
他冷笑着坐在椅子上,手里熟练地把玩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说:“你若是不说,我就废了你。”
我当时是真怕他把我弄死,毕竟,我和老皮被抓进来的时候,没有别人知道。
我跪在地上,背铐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跪了也最少三个小时了,头上的汗水比五月里在麦田里割麦还要澎湃。
我的头几乎垂到地上,试图卸载背铐带来的巨大痛楚。
张玉奎坐在凳子上,用皮鞋尖勾住我的下巴说:“你不说也行,只要你说了那个老皮的事儿,就算你立功了。”
我还是不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一共才跟着他不过半年,但是这半年里,我却见过他给要饭的兜里塞过钱,扶起过被车撞倒的老人。
张玉奎折磨了我一会,然后就出去了。
我和老皮受审的距离不远,我估摸着也就是另外一个房间。因为张玉奎一出去,老皮挨打的声音就顺着房角用来串线留下的小孔清晰地传过来。
过了很久,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我会被渴死,打死,折磨死,于是我说:“我和老皮还盗窃了很多……”
当然这是我瞎编的,根本就是胡诌来的,可是他们很是惊喜,一字不落记录下来,或者诱导我说出更多。
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他们终于哈欠连天,让我在记录上摁了手印,签了名字。
6
这些人可能是去睡了,把我一个人拷在冰冷的暖气片上,我坐在地上,整个人昏昏沉沉仿佛开始做梦,极度口渴和身体的疼痛让我真想以死解脱。
早上八点的时候,张玉奎带着几个人过来,把我塞进了警车,在车里我看到了老皮。
他冲我笑笑,说了一句:“还好吧?”
还没等我回答,张玉奎就把他的头死死摁在地上,他佝偻着,瞬间倒在地上,没有反抗,也没有挣扎,像是一条濒死的狗在等着上帝的召唤。
进了县看守所,我和老皮被干警们抽去了皮带和鞋带,后来才知道那是防止我们自杀用的,当然这只是站在我们立场上的说辞,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怕有人利用皮带越狱,因为后来我听说,在我进去之前,就有一个犯人用皮带系住窗户上两根相邻的铁棍,然后用一把筷子搅动皮带,竟然拉开了铁棍,越狱了。
同案犯不能分到一个号子,我分到了,老皮分到了。
因为昨晚一晚没睡,我到了,看到橱柜上不知是谁放着的一塑料饭盆水,我冲上去,一把端起,瞬间就灌到了肚子里。
饭盆一扔,我终于坚持不住了,一下子倒在大通铺上,昏昏沉沉中听见有人说:“奶奶的,这家伙不知道规矩,把他拉起来开堂!”
接着又听见有人说:“慢着,看看他是不是被老警察洗了。”
接着我就感觉到我的上衣被掀开,我的裤子被扒下,再接着传来一阵阵唏嘘声,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7
当我醒过来时,已经是晚上晚饭的时候,几个犯人把我摇晃醒,我的面前已经放了一盆玉米面糊糊和一个拳头大小的窝头。
后来他们说,看我昏睡了一整天,怕醒不过来,就叫醒了我。
我端起一碗玉米面糊,喝了一口,没咽下去就喷了出来,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堵塞住了一般。
几个犯人纷纷侧目,其中一个个子很高的犯人走过来,让我张开嘴,他看了看说:“没事,就是被老警察用电棍来了一个深喉,肿了。”
这些人跟我很快就亲近起来,尤其是那个高个子男人,他是我们号里唯一的一个带着手铐脚镣的犯人,那是重刑犯特有的待遇,后来我才知道他竟然是我们县建国以来最大的盗窃团伙主犯,赵凤军。
还有一个带着脚镣却没戴手铐的胖子,叫崔三爷,沙河人,他是当年上了央视的双龙帮三当家,后来被执行了死刑。
赵凤军是号长,崔三爷是炕头,就是负责所有人的值班内务问题。
晚上,看守所里不关灯,九点之后开始就寝,赵凤军躺在被窝里问我:“你的案子是经谁的手?”
我没有被子,崔三爷不知道从哪里给我捣鼓了一床被子。由于我是新犯人,第一晚需要值班,我就披着被子坐在凳子上,待在赵凤军的头前。
我说:“是张玉奎。”
赵凤军和崔三爷对视一眼哼道:“又是这个稀毛。”
赵凤军说:“遇到他你就算是遇到阎王爷了,这看守所里一共十二个号,你问问,凡是刑事案件的,只要经他的手,就没有能够囫囵下来的,哪个不是阎王殿里走一遭?”
8
赵凤军越说越激动,他忽然站起来,一把脱掉自己的内裤,我惊呆了,垂在他胯间的生殖器像是一只烤焦了的家雀,漆黑,无力。
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就是张玉奎用电话线给我电的!”
怪不得赵凤军的身上总有一股尿味儿,原来那东西已经只是个摆设了。
赵凤军刚钻进被窝,崔三爷冷笑一声说:“你那算啥,当年张玉奎对我熬鹰,老子整整坚持了六天六夜。”
熬鹰,是清朝时期从关外传过来的一种驯化鹰的办法,就是不让它睡,从意志上彻底瓦解它。
据崔三爷说,当时为了得到他的案底,张玉奎一不打他,二不骂他,而是熬他,七天七夜,饿了有饭,渴了有水,倘若你困了,就是一棒子,再困,就是电棍深喉电话线,一应俱全地招呼。
崔三爷身负几条命案,又兼抢劫强奸重伤等,说出来就是一死,所以,他一路从邯郸那边押解过来,啥样的刑罚都吃过,唯独没有吃过张玉奎发明的熬鹰。
第七天的时候,崔三爷忽然出现了幻觉,他说,他亲眼看到他的饭盆里出现了一群小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饰从里面跳出来,围着他吹拉弹唱,他还看到,档案柜忽然开了,几个古代的穿着铠甲的武士在他面前吃火锅……
意志力被瓦解,思想就乱作一团,他的防御意识远不如一只鹰,被彻底瓦解。最终他就像是竹筒倒豆子一般,你问我答,没有一句谎话地把自己所犯的罪行来了一个彻底交待。
我很快就跟他们打得火热,尤其是几个被张玉奎打过的人,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咒张玉奎早点死去,甚至问候他的家人们。
9
可是,这种情形没过几天,我忽然患上了一种病。
这种病一开始只是刺痒,从小腹,到指缝,到脖子,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绿豆大小的红色疹子,一挤,里面就有白色的或者黄色的汁液流出来。
那种痒,钻心,真想把一层皮抠下来,等到过了半个月之后,下身竟然也布满了结节。
所有的犯人开始远离我,因为他们都看到我痒的时候,把身体抓得血淋淋的。赵凤军及时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看守所的曹管教。
曹管教是个复原军人,个子不高,脸上黢黑,说起话来梗着脖子,人特别正直。
医院,可能是看到我戴着铐子的缘故,医生们很不耐烦,当然也很不齿,他用镊子在我的生殖器上扒拉了几下说:“你这是性病的一种,是尖锐湿疣,有传染性,建议隔离。”
我想起了那一晚,和老皮去那个洗头城的一夜风流,肯定是那个女人使得我染上了那种病。回到看守所,我马上就被单独关押到一个号子,也就是紧挨着老皮号子的号。
号其实是一个仓库,里面都是以前犯人们走了之后留下的衣服被褥脸盆等东西。
号子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用来睡觉的大通铺,另一半是一墙之隔的笼区。从屋子里侧的小门出去,就是一个有七八平方的铁笼,这是犯人们平时抽烟放风的地方,角落里是厕所。
我以前和老皮距离较远,没有对话过,现在我们俩只隔着一道墙,而且笼子上方没有封闭,我们两人说话即便是不用太大的声音都能听见。
老皮敲了敲墙壁说:“二子,我们是不是被算计了?”
他说:“我们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彭玉花之后,就被抓了?难道这彭玉花是警方的卧底?”
我不信,亏他还睡了人家彭玉花。
老皮问我:“挨打了吗?”
我说挨了。
老皮笑着说:“是那个叫张玉奎的吧,我在隔壁都能听见你的惨叫声。”
10
我和老皮的案子进展得很快,一个多月,就从收容审查到了批捕。
已经过了元旦,如果不出所料,年底我们的案子可能就要开庭。
那一晚半夜,我忽然听到一阵铁门哐当的声音以及钥匙盘撞击的声音,按照惯例,这深更半夜开门就是送来了犯人。
号的监舍门开了,只听曹管教说:“都睡觉,这个人谁也别动。”
“谁也别动”,这是一句潜台词,意思是这个人有关系。
有关系的人多了,有一次看守所长的80岁的叔叔因为嫖娼被关了进来,人家在里面就是大爷,像住养老院一样,晚上还能坐所长的车回家喂喂猪。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忽然乱了起来,有人使劲踹着铁门大喊着:“所长,快救命!”
我一激灵从炕上爬起来,警觉地听着隔壁的动静。
这么一闹腾,负责传话的劳动号急忙跑到所长值班室前敲门说出事了。
等外面嘈杂的一切结束之后,天色已经微微亮了。
笼区传来了轻微的踹墙声。
我裹着被子跑出去,那边传来了老皮抑制不住的兴奋:“我们这里死人了,就是昨晚刚送进来的那个犯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据说是偷了矿上一盘电缆,被张玉奎打死了。”
据老皮说,那人进来之后一个劲儿地吐血,他一边吐一边骂张玉奎,说:“老子那电缆不是偷的,是买的。”
老皮心里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他知道这张玉奎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肯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先不说他能不能被判死刑,但是他这身警服肯定要脱下来了。
这个人的死算是为我们所有被张玉奎打过的犯人集体报了仇。
11
第二天,县里和市里来了好多警察,来看守所号监舍调查有没有曾经对这个死去的犯人二次伤害。
曹所长以他的人格担保,死者没有受到伤害,因为他千叮万嘱说,这个人伤势很重,本来不敢收押,是刑警队的张队长亲自签署了看守所无担责证明。
犯人们更精明,凡是被张玉奎照顾过的人他们都当成是自己人,更不用说这个被张玉奎折磨得大口吐血的犯人了,那在他们心里更是英雄般的存在。
那一天,所有的犯人们都在庆贺,庆贺张玉奎即将受到惩罚。看守所的犯人像是过年了一样,热烈的气氛隔着一道道墙我都能感受到。赵凤军托送饭的劳动号给我带来了一根指头粗细的王中王火腿,还有一句话:兄弟,你信因果报应吗?
那晚,老皮也很兴奋,他给我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
等到岗楼上的武警们换了两点的岗之后,老皮忽然说道:“二子,你这传染病可以保释的,你找人活动一下吧。”
我说:“老皮你知道的,我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也没有多余的钱了,找谁活动?”
正在说着话,我的监舍的铁门忽然响了起来。
这个监舍只关着我一个传染病,一般干警都嫌弃,根本就不会过来。现在这半夜的竟然有人开门,难道是又给我送进来一个传染病罪犯?
我走进屋里,就见几个干警和几个穿着便装带着口罩的人涌了进来,其中有几个人拎着被子、暖瓶、奶粉、糕点等。这倒像是一个强大的住院陪床团。
这些人并没有过多声张,而是迅速地铺好被褥,摆置好物品,这才看着我声色俱厉地说:“照看着他点,否则……哼哼……”
求人都这么拽?是威胁我吧,又无冤无仇的。
那些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然后迅速退了出去,瞬间,监舍的门关住了,监舍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穿着西装、瘦瘦小小带着硕大口罩的人。
这个人不简单。
因为那些干警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不仅不是押他来的,相反还是为他服务,为他抻床铺,为他冲奶粉。
这时,这个人慢慢坐到床上,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支。烟是好烟,传说中的软中华。
他点燃一支,接着摘下口罩,我顿时惊呆了,这个人正是差点置我于死地被万千犯人唾骂、恨他不死的张玉奎。
张玉奎冲我笑了笑,然后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将那包烟塞给我说:“你拿着抽吧,哎,你认识我吗?”
12
他已经忘了一个多月前被他打得死去活来的我了。
我看着他,也笑笑说:“不认识。”
我假装问他是谁,他搔了一下稀稀疏疏的几根头发说:“我就是一个某单位的会计,这不算错了账,来配合调查。”
我并不挑明,那样对谁也不好,至少现在我在明处他在暗处。
隔壁又有人在踹墙,我走到外面,老皮问我:“怎么你那隔离监舍还关进了一个外人?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
我刚想把这件事告诉老皮,一回头却发现,张玉奎正在盯着我。
我不知道张玉奎和我在一个监舍这件事捅出去的后果,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将会受到很多人的问候。
比如,赵凤军,比如崔三爷,比如老皮。
我不敢,因为刚才那些人的恐吓,还有,我估计真要是单挑,我这个十八岁的身板也肯定不是刑警队长张玉奎的对手。
我也不能,因为现在人家张玉奎有的我都有,包括一天一只的烧鸡,一天一包的中华,一天一袋的鲜奶等等,我承认,我在家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张玉奎对我很好,他竟然把自己的缎面大花被子给我盖,而且还把他那据说一百多一个的裤头给我穿。
一开始我还暗暗得意:老子的病传给你正好,就算是报了当日他折磨我的仇了。
可是他对我越来越好,甚至不避讳和我睡一个被窝,而且还给我存了一张一千元的卡。我在看守所也算是富翁级别的人物了。
但张玉奎似乎有点变态,竟然穿我穿过的衣服袜子,甚至内衣。
当然我不会因为他对我好,就忘记了他曾经践踏过我的尊严,忘记他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形。
因为我不抽烟,而老皮又是烟鬼,所以我就在笼区里把一包包的中华从笼子上方的缝隙里扔过去。
号子那边传来了一阵阵惊呼,老皮踹着墙激动地问我:“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犯人是不是一个大款?要知道这中华烟据说都七八十一包呢。”
我没回老皮。
宁肯沉默,不愿撒谎。
13
隔三差五地,就会有人直接来监舍和张玉奎见面,这些人每次都带着口罩,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每次一来,我就会被驱逐到笼区,他们不走我不能回来,有效地避免了他们的谈话被我听到。
很快,我就发现张玉奎也染上了我的病,从他晚上刺啦刺啦的挠声里,我就知道他有多痛苦。
我真想把这件事告诉老皮,与他分享和我一样的快乐。
距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一个早晨,监舍忽然来了好多人,有警察,有医生,有穿着便装的,他们像是来过年一样,嘈杂而热闹。但是又和来的时候不一样,因为这次张玉奎走了,他的那些东西都留下了,包括抽了一半的中华烟,喝了一半的芝麻糊,拆了一半的方便面,以及被褥、脸盆和整箱的火腿肠,他什么也没带,只是冲我笑笑说:“二子,这些东西留给你了。”
他竟然早就认出了我!
张玉奎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两天,曹所长在监舍前,递给我两包药膏,让我涂抹在身上,说三天之内我的性病就会好。
这药很神奇,第三天的时候,果然我身上的病灶全部除掉了,整个人犹如新生了一般。
我很感谢曹所长,他却笑笑,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和老皮被判刑,他判了十年,我因为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从轻处理,判了六年。
服刑完毕,我出狱的时候,老皮来监区看我,他说让我出去一定要找到彭玉花,问问是不是她出卖了我们。
他还记得这件事,肯定也记得张玉奎,因为我看到他在撒尿的时候,那胯间的生殖器和赵凤军的一模一样。
我回家之后不久,遇见了已经退休了的曹所长,感谢他当年给我的药物,治好了我的性病。
曹所长摇头说:“你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性病,而是疥疮,那两袋药膏也不是我给你的,而是张玉奎给你的。”
我愣了一下问:“张玉奎,他现在人呢?”
曹所长脸色暗了下来,小声说:“死了。”
“死了?”
“是的。”
那年,张玉奎从我身上故意感染了疥疮,却以性病保外就医。被开除公安队伍的他,有一次去嫖娼的时候,竟然还吓唬一个小姐,说让她按照他的意愿来摆各种姿势,女人不从,他就吓唬她说:“要是当年,老子把你抓走,像折磨老皮一样熬鹰,怕你不得跪下来求我。”
因为这句话,骇得那个女人情急之下,失手将他推下了楼。
“这家伙也算是罪有应得吧。”我小声说道。
曹所长摇头说:“还有更加巧合的,你知道这个摔死他的女人是谁吗?”
“她叫彭玉花。”
题图
图片来自《叛狱无间》
配图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
(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互动话题
他是以权谋私的队长,非法审讯、虐待犯人,是个恶人。可他似乎对“我”网开一面,诸多照顾,如果纯粹恶,本不必做那些事。
今日话题:你觉得,张玉奎为什么给“我”留药?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往期推荐
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