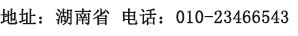这种疾病的运动根源是没有分殊的,但是因其穿越的空间和在身体表面显现的部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
“它们在胃里积聚,然后突然涌到咽喉部的肌肉,在所穿越的整个区域造成痉挛,在胃里造成肿胀,如同一个大球。”歇斯底里在稍高的位置上,“侵袭结肠以及心脏下面的区域,引起难以忍受的疼痛,很像骼骨区的疾病。
”如果该病升得更高一些,就会侵袭“中枢部位,引起剧烈的心悸。病人此时确信,护理人员应能听到他的心脏撞击肋骨的声音。
”最后,如果疾病侵袭“头部的外围、头骨之间的部分,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引起刚烈的疼痛,并伴有剧烈的呕吐。”身体的各个部位因本身的情况和特点而决定了症状的不同表现。
因此,歇斯底里显得是最真实又最有欺骗性的疾病。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以动物元气的运动为基础的;但它又是虚幻的,因为它所产生的症状似乎是由器官内在的无序造成的,而这些症状其实是一种中枢的或普遍的无序在器官层面上的形成物。
正是一种内在流动的错乱在身体的表面表现为局部症状。器官实际上是被无序而过分的元气运动所侵扰,但却装作自己出了毛病;从内部空间运动的某一缺陷开始,器官完全模仿自身才会产生的错乱;
歇斯底里用这种方式“模仿出人的肉体的几乎所有疾病,因为它在人体中无所不在,它能立刻造成符合该部位的症状。如果医生既不聪慧又无经验,就很容易被欺骗,会把歇斯底里的症状归因于该部位的某种常见病。
这种病的策略就是,它以同一形式的运动穿越肉体空间,表现出不同的外观,但是这里的性状不是本质,而是身体耍的一个花招。
体内空间越容易被渗透,歇斯底里就越频繁,其外观也越变化多端;如果身体健壮,抵抗力强,如果体内空间紧密,而且不同区域的质地参差不齐,那么歇斯底里的症状就很罕见,其效果也单一。
不正是这一点使女性歇斯底里与男性歇斯底里,或者说;使歇斯底里与疑病症有所区分吗?实际上,不是症状,也不是病因,而是身体的空间坚实性或者说内部密度构成这些病的区分原则。
“除了由可感觉的各种部件组成的所谓‘外在的人’,还有一个由动物元气系统构成的‘内在的人’,后者只能用精神的眼睛看到。后者与体质紧密相联,因人的状态不同而或多或少有些紊乱,其程度取决于构成这架机器的本原的自然坚固性。
这就是为什么步入比男人更容易受到这种病的侵袭,因为女人的体质更纤细而不那么坚固,因为她们过着较温和的生活,因为她们习惯于舒适的生活,而不习惯于受苦。”
就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已经包含着空间密度的一个涵义:它也是一种道德密度;器官对元气的无序渗透的抵抗力可能也是灵魂保持思想和欲望的井然状态的能力。
这种变得疏松的空间,可能完全是心灵的松懈造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惯于艰苦劳作的女人很少患歇斯底里,而当她们生活舒适、闲散时,或当某种悲苦压倒她们的意志时,就非常容易患歇斯底里。
“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在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急的是一种歇斯底里。”
这样,我们就对古老的道德直觉有了一个新的概括。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起,这种直觉就把子宫当作一个有生命的、运动不止的动物,并且对其运动的空间加以规定;
这种直觉在歇斯底里中感受到一种不能控制的欲望骚动,因为病人既不能满足它们又不能驾驭它们;女性器官意象上升到胸部和头部的说法反映了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三元说中的一种剧变和力图确保自身静止不变的等级序列中的一种剧变。
对于西德纳姆来说,对于衡卡儿的信徒来说,道德直党始终如一,但是借以表达道德在觉的空间画面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的垂直的等级秩序被一个立体空间所取代。这个空间被不停的运动来回横切。
这种无序的运动不再是底层上升到高层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混乱空间中的无规律的旋风。西德纳姆试图用“精神的眼睛”洞察这个“内在的身体”,因为它不是客观视察的迟钝目光所能看到的客观身体,而是一个场所,在那里,一种想像这种身体和译解其内在运动的方式同一种赋予它道德价值的方式紧密结合。
在这种伦理知觉层次上的发展到此完成。在这种知觉中,一贯柔顺的医学理论意象发生了曲折和变化;在这种知觉中,重大的道德主题也得到系统的表达,并逐渐更新了原初的面貌。
然而,这种易渗透的身体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疾病在各器官的弥散反过来说则是一种允许其扩散并连续影响各器官的传播运动的结果。
如果说疑病症患者或歇斯底里患者的身体是一种疏松的、自我分离的、因疾病侵袭而膨胀的实体,那么这种侵袭则必须借助于某种连续空间才能实现。疾病借以循环流动的实体应该有不同于扩散的症状借以显现的身体的特性。
这个问题困扰着18世纪的医学,导致人们将疑病症和歇斯底里视为“神经方面”的疾病,即一切交感作用的一般媒介的原发病。
神经纤维被赋予某些引人注目的特性,从而能够将异质因素整合在一起。神经传送着各种迥然不同的印象,而它在任何地方、任何器官里都应该有同一性质。这样说能不令人惊异吗?
“神经在眼珠后面的伸展使人能够接收微妙的光亮;听觉器官的神经对发声物体的振颤十分敏感;但是就性质而言,它们与触觉、味觉和嗅觉等较迟钝的感觉神经毫无区别。”
这种功能各异而性质同一的特性,保障了相距最远的和生理上调然不同的器官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
“人体神经的同质性以及各种相互维系的器官之间的无限交流……确立了器官之间的和谐,从而常常导致一处有病,多处受害。”
但是,更令人赞叹的是,同一神经纤维能同时传送某种无意识运动的刺激和感觉给器官留下的印象。梯索(Simon-Andr6TISS。t)认为,这种同一神经的双重功能是两种运动的结合。
一种是造成无意识刺激的波荡运动(“这是一种装在弹性容器中的液体运动,比如,液体装在皮囊中,挤压皮囊,液体就会通过一个管道喷出。”)另一种是造成感觉的粒子运动(“这是一连串象牙球的运动。”)因此,同一神经能够同时产生感觉和运动。
正如我们在各种神经疾病中观察到的,神经的紧张和放松都会同时改变那些运动和感觉。然而,尽管神经系统有这些统一的性状,
我们是否就一定能用神经纤维的实际网络来解释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如此纷繁的紊乱之间的内在联系呢?如何来设想披露了某种神经疾病的各个部位的症状之间的联系呢?
如何通过探究这种联系解释某些“极其敏感”的女人会因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听到关于一个悲惨事件的生动描述或看到一个厮杀场面而“晕厥”?
人们的探寻是徒劳无益的: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神经联系,也没有发现任何从这种根源延伸出来的途径,而只是发现了一种基于生理相关性秩序的、间接的作用。
这是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十分确定的官能,这些官能要么是普遍的,遍及整个人体,要么是特殊的,主要影响某些部位。”
感觉和运动的双重官能使器官互相交流、同甘共苦,并能对来自远处的刺激做出反应。这种特性就是交感作用。实际上,怀特既未能将交感作用完全归因于整个神经系统,也未能从与感觉和与运动的关系上来界定它。
交感作用在器官中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它在那里是否能通过神经的中介而被接收到;神经越灵活,交感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与此同时,交感也是感觉中的一种:“各种交感都以情绪为前提,因此只能透过神经的中介而存在,而神经完全是感觉借以运作的上具。”
然而,神经系统在此不是被用于解释对运动或感觉的传送,而是被笼统地用于确认身体对自身现象的敏感性、确认身体在肌体空间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共鸣。
神经疾病本质上是交感的混乱;其前提是神经系统的普通警觉状态,这种状态使各个器官都可能与其他器官产生交感:
“在神经系统的这种敏感状态下,刻骨铭心的激情、饮食习惯的破坏、气候冷热湿闷的突然变化,都很容易产生病状;在那种状态中,人们也不能保持身体健康,通常会有各种连续不断的疼痛感。”
无疑,这种过度的敏感都会伴有迟钝、困倦;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
“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
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自我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神经疾病。
“女人的身体系统通常比男人更灵活,因此更容易患神经疾病,而且女人的神经疾病也更严重些。”怀特言之凿凿地说,他曾目睹“一个神经脆弱的少女因牙疼而昏厥,持续几个小时不省人事,直至疼痛更剧烈时才醒过来。”
神经疾病是相连肉体的疾病。自我感觉过于敏感的身体,各部位过于紧密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思议地紧缩的肌体空间,此时已成为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共同母题。
对于某些人来说,身体与自身的亲密关系表现了一种准确的意象,如庞默所描述的“神经系统的萎缩”。这重意象掩盖了问题,但是并未抹煞问题,也未妨碍有关努力的继续展开。
这种交感究竟是各个器官中所蕴藏的一种性能——切恩所说的“情绪”,还是一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播?这些神经疾病的相似病状究竟是这种情绪的受激状态,还是这种间质性身体活动性增强的表现?
18世纪,当生理学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界定神经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敏感性和应激性;感觉和运动)时,医学思想中的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十分典型的现象是,医生们按照一种与生理学提供的图式大相径庭的图式将上述观念组合起来,不加区分地应用于笼统的病情诊断。
敏感和运动是不能分开的。
梯索解释道,儿童比其他人更敏感,因为他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比较轻,也比较活跃;应激性(irritability)按哈勒的理解是神经纤维的一种性能,等同于激怒、烦躁状态(发炎)(irritation),被认为是一种持久的刺激引起的器官病状。
因此人们公认,神经疾病是过敏与神经过分活跃的结合物。
“人们有时会看到,一个极小的刺激会在某些人身上产生比健康人强烈得多的运动;这种人经受不住任何微小的反常印象。极其微弱的声音和光亮都会给他们造成异常的症状。”
由于刻意保留了社ritation观念的多重含义,18世纪末的医学就能有力地证明气质(应激性)和病变(烦躁、发炎)之间的连续性,而且还能同时维系两个观念。
一个观念是,各个器官在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一般侵袭时会产生独特的紊乱(器官特有的敏感性决定了这种侵袭是一种不连续的传染)。
另一个观念是,任何一种紊乱都能侵袭肌体的各个部分,从而在肌体内传播(神经纤维的活动性造成了这种不间断性,尽管各个器官的神经纤维有所不同)。
然而,如果说“受激神经”的概念确实起了一种默契的混淆作用,那么它也造成了病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区分。
一方面,神经疾病患者是非常易于激动的,即他们十分敏感,神经脆弱、肌体敏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极易产生强烈的交感。
这种全面的共鸣——感觉和身体活动兼而有之——构成了这种疾病的首要决定因素。女人“神经脆弱”,无所事事时很容易沉溺于想像,男人“因劳作而比较刚健’,因此女入比男人更易受到神经疾病的侵袭。
但是,这种过度烦躁有其特点:它会减弱甚至温灭灵魂的感觉;仿佛神经器官的敏感性便灵魂的感受力不堪重负,并且自己留下了因自己的极度活跃而引起的大量感觉;
神经系统“处于这样一种烦躁和反应状态,因此不能将自己的体验传送给灵魂;它的全部印象都是混乱的;它不能理喻它们。”
这样就出现了非感觉的敏感性的观念,这种由灵魂和肉体衍生出来的敏感与阻止神经刺激抵达灵魂的感觉麻木成反比关系。
歇斯底里患者的丧失知觉不过是过于敏感的反面。这种关系是交感慨念所无法界定的。它是由应激性概念派生出来的。当然,在病理学家的思想中,这种关系几乎未加阐明,依然混淆不清。
然而,“神经疾病”的道德意义却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人们把神经疾病与辅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联系起来(甚至是由各种模糊不清的交感渠道联系起来的),这些疾病也就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中:
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从此,人会因感受过多而生病,会因与周围的一切过于密切而生病。人不再受自己的秘密性质所驱使,而成为世界表面的一切诱惑肉体和灵魂的事物的牺牲品。
结果,人变得更无辜也更罪孽深重。
更无辜,是因为人被神经系统的全面烦躁推入不省人事的状态,其程度与病情成正比。更罪孽深重,是因为他所依恋的万物、他的生活、他曾患过的疾病、他曾洋洋得意地酿造的感情和想像,部汇聚在神经质的烦躁之中,这既是它们的正常后果,也是对它们的道德惩罚。
全部生活最终根据这种烦躁的程度来评判,其中包括非自然的习弊,城市中的蜗居生活,读小说,泡戏院,渴求知识,“过强的性欲,或其它既伤害身体又为道德所不容的犯罪习性。”
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神经烦躁的神经病人,其无辜根本上正是对一种更深刻的罪孽的正当惩罚:这种罪孽使他抛弃自然而投身尘世:
“多么可怕的状态。这是对一切柔弱灵魂的折磨,懒散使他们敢于犬马声色,他们摆脱自然所要求的劳作而拥抱思想的幻影。……富人便是因滥用其财富而受到这样的惩罚。”
到此我们已经站在19世纪的门槛。
在19世纪,神经应激性将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交上好运。但是,它目前在神经疾病领域中毕竟留下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完全确认。由于对敏感和感觉的重大区分,这两种病进入了非理性领域。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非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
只要种经状态是惊授状态或是奇妙地穿越身体的交感状态,即便导致意识减退和丧失,那也不是病癫。但是,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便出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确认赋予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率、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而这种内涵根本不属于古典主义的体验。它还使非理性担负起这些新的价值:不是位盲目成为各种疯癫现象出现的条件,而是把有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
由此危及了以往非理性经验中的根本要素。
以往被视为盲目的将变为无意识,以往被视为谬误的将变为过失。疯癫中表示非存在的吊诡现象的一切,都将变为对道德罪恶的自然惩罚。
总之,构成古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诸妄,都将土崩瓦解,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
19世纪的“科学的精神病学”指日可待了。
正是在这些很快就会受到嘲弄的“神经疾病”和“歇斯底里”概念中,产生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病学。
第六章,医生与病人
医院里并未推行,医院的主要宗旨是隔离或“教养”。然而,在医院之外,对疯癫的治疗在整个古典时期都在继续发展。
长期疗法形成了,其目的与其说是医治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医治其神经纤维及其幻想过程。疯人的身体被视为明显而确实的疾病显现部,由此产生了物理疗法,而其意义则借鉴自关于肉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疗法。
1.强固法。
疯癫即使表现为最骚动不安的形式,也会有一种虚弱因素。如果在疯癫对精神元气陷于无规律运动之中,那是因为精神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重量来遵循自然轨迹的引力作用。
如果在神经疾病中经常出现惊厥,那是因为神经纤维太脆弱,太容易激动,或者说对振动太敏感。总之,神经不够坚强。明显的疯癫狂乱有时似乎使躁狂症者力量倍增。
但是,在这种狂乱之下,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虚弱,即缺乏抵御能力。疯人的躁狂实际上只是一种消极的暴力行为。因此需要有一种能使精神或神经纤维获得活力的疗法。
但这是一种沉稳的活力,任何混乱都不能奈何它,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服从自然规律的进程。这种活力不仅表现为生机勃勃,而且表现为一种坚强性。它战无不胜,以一种新的抵抗力、青春的灵活性包围住对象;同时它又受到控制和驯化。人们应该在自然中寻找一种力量来增强自然之物本身。
理想的医治方法应该能“扶持”精神元气,“帮助它们克服使其骚动的发酵因素”。扶持精神元气就是抑制精神自身无法控制的无益的躁动,还应使它们能够避免出现引起亢奋和骚扰的化学鼎沸状态,
最后应使它们坚实起来,足以抗拒企图窒息它们、使它们怠惰和陷入晕眩的烟气(忧郁气)。“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可以增强精神元气,对付忧郁气。
令人不快的感觉能够刺激精神,从而使精神产生反抗力并迅速地汇集到反击忧郁气侵袭之处;“阿魏、唬柏油、烧焦的皮毛均可以用来(达到这一效果)。总之,凡是能使心灵产生强烈不快感觉的东西均可起作用。”
对付发酵作用,必须使用解毒剂,如抗癫痛的查拉斯,最好是用众所周知的匈牙利工后水。消除腐蚀酸以后,精神就恢复了。
最后,为恢复精神的正常运作,朗格建议,让精神受制于令人愉悦的,适度的和有规律的感觉和运动:“当人的精神涣散时,应给予必要的治疗,使其平静下来,恢复正常状态。惬意的气味,在景色宜人的地方散步,见到惯会给人开心的人,另外还有音乐,这些都能使人的心灵感到温馨愉悦。”
这种稳定的温柔,适度的力量以及完全为了保健的活跃,都是使机体内连结肉体与灵魂的脆弱因素变得坚实的手段。但是,也许最有效的强身方法是使用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应该既十分坚实又十分柔软,既有极强的剧性,又能使懂得如何使用它以达到自己目的者任意摆布它。这就是铁。铁凭借其特有的性质,集上述相互矛盾的品质于一身。
其他物质都没有铁的那种刚性,也没有铁的那种可塑性。铁是大自然的造化,但又可由人的技术摆布。除了用铁之外,人类还能有其它更可靠的方法——即更接近于自然而又更项从人类的方法——来加强自然之物,使其具有充足的力量吗?
人们常引用迪奥斯科里斯的一个古老例子:当他把一块烧红的铁块扔进水里后,就使静止的水具有了本身所不具有的活泼性。火的炽热,水的平缓流动,经过处理而变得柔顺的金属的活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使水具有了强化力、激活力和加固力。
水能把这些力量传递给人的机体。即使不经过任何加工,铁也能起作用。西德纳姆推荐最简单的办法,即直接服用铁锉屑。怀特举例说,有一个人因胃神经虚弱而长期患疑病症,为了治病,他每日服用二百三十二眼铁。
这是因为,铁除了其他优点外,还能直接自我传递。它所传递的不是物质而是力量。似乎矛盾的是,虽然它有很强的刚性,但它能直接溶于有机体内。沉淀在有机体内的是铁质,而毫无铁锈或铁渣。
很显然,铁能创造奇迹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各种奇想,并压倒了观察本身。如果人们进行实验,那么其目的不是发现一系列的实证效果,而是为了强调铁的品质的直接传递功能。
赖特给一条狗喂铁盐。他发现,将乳康同五倍子(gall)颜料混合,一小时后乳糜并未显示出吸收铁局必然显示的紫色。可以肯定,铁没有进入消化过程,没有进入血液,实际上也没有渗入有机体,而是直接作用于腹壁和神经纤维。
精神和神经纤维的加固,不是一种观察到的效果,而是一种有效的比喻。它意味着,无须任何扩散运动,便可以传递力量。接触便能提供力量,而无须任何交换或物质、任何运动交流。
2.清洗法。
针对疯癫的各种病症产生了一系列疗法。这些病症是:内脏堵塞、错误观念泛滥,忧郁气沸腾,暴力行为,体液和精神腐败。而这些疗法都是一种清洗手术。
理想的疗法是彻底清洗。
这种方法最简单,但又最不可能用于治疗。该方法是用一种明亮清洁的血液置换忧郁症患者过量的、粘滞的、被苦涩体液所渗入的血液,因为清洁血液能驱散话妄。
年,霍夫曼建议用输血来治疗忧郁症。几年后,该想法已得到一定的承认,因而伦敦哲学协会制定了计划,对禁闭在贝德拉姆的病人进行一系列实验。受命从事这项工作的医生爱伦(Alien)拒绝这样做。
但是,丹尼斯对自己的一位病人——失恋忧郁症患者进行了试验。他从病人身上抽出十盎司的血,然后输入稍少一些的取自小牛大腿动脉的血;次日,他重做一次,但换血量仅几盎司。
病人开始平静,过了一天便神智清醒了,不久便完全康复了。“外科医生学会的全体教授都确认这一试验”。尽管后来还有几次试验,但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抛弃了。
人们乐于采用的药物是防腐剂。
这是因为“用没药和芦荟保存尸体已有三千多年的经验了。”
难道尸体的腐烂不是与体液疾病所导致的身体恶化具有同样的性质吗?那么,最值得推荐的抗忧郁药物就是没药和芦答了,尤其是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的著名药方。
但是,仅仅阻止腐烂是不够的,还应根除腐烂。因此产生了防止变质本身的疗法,或者旨在转移腐烂物质,或是旨在溶解腐烂物质。这就是偏转术和洗涤术。
第一种包括各种严格意义上的物理方法。
这些方法旨在身体表面制造创伤或疮疖。这些创伤或疮疖是缓解肌体疾病的感染中心,向体外排病的中心。
法洛斯(Fallowes)就是这样解释其“橄榄油”的有效机制:在疯癫中黑色忧郁气堵塞了元气必经的细小脉管,因此血液流动失调,滞留于脑血管内。必须有一种“能使注意力分散”的迷惑运动,才能使血液活跃起来。
“橄榄油”就具有促使“头上长小脓疮”的效用。在脓疤上涂上油,防止变干,这样“滞留在大脑的黑色忧郁气”就可以连续排放。当然,烧灼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有人甚至认为,像疥疮、湿疹、天花等皮肤病,也能终止疯癫的发作,因为这种病能使内脏和大脑的腐烂病变转移到身体表面,向外排放。
到该世纪末,人们已经习惯于给最顽固的躁狂病人注射疥疮液。医院总管写的“年训示”中建议,如果放血、药泻、浸泡和淋浴都对躁妄症无效的话,那么采用“烧灼术、切口排液、制造表皮脓疮和注射疥疮液”将能奏效。
然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消解体内形成的、造成疯癫的发酵因素。为此,主要药物是苦药。苦药具有海水的全部涩厉特点。它能通过洗蚀来达到净化目的。它磨蚀疾病在肉体和心灵中所沉淀下的各种无用的、不健康的和不纯净的东西。
咖啡有苦味和活性,因此可用于“体液粘滞的肥胖者”。咖啡有干燥作用,但不会燃烧,因为这种物质的特性是能驱散多余的湿度,却又不会产生危险的燥热。咖啡里就好像有火却无火焰。它是一种不靠焙烧的净化剂。
咖啡能减少不净物:“喝咖啡的人根据长期体验,觉得它有助于恢复胃的功能,除湿祛风,消痰通便,尤其是防止浊气上升,从而减少病人通常感到的头痛。最后,它使元气变得强健有力和清纯,而对那些常饮用者也没有留下任何灼热感。”
同样具有苦味和滋补作用的是奎宁。
怀特经常让那些“神经系统十分脆弱”的人服用奎宁。奎宁对医治“虚弱、沮丧和消沉”很有效。在为期两年的疗程中仅用一种奎宁药酒,“偶尔停用,但停用不得超过一个月”,用此方法便可治愈神经不适的妇女。
对于神经脆弱的人,奎宁必须与一种“味觉舒适的苦药”配在一起服用。但是如果病人不怕强烈的刺激,那么最好服用奎宁硫酸。二十至三十滴奎宁硫酸的效果为佳。
十分自然的是,肥皂及肥皂制品在清洗疗法方面必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效果。因为“肥皂几乎能溶解任何凝聚物”。
梯索认为,直接服用肥皂可以镇抚许多神经性疼痛;最好是,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服用肥皂,或者与面包、“滑腻的水果”,如樱桃、草毒、无核小葡萄干、无花果、葡萄、梨子以及“同类水果”,一起服用。
但是,也有些病例十分严重,其梗阻难以克服,服用任何肥皂都无能为力。对此,可用可溶性酒精。马泽尔(Muzzell)是最先想到用酒石来医治“疯癫和忧郁症”的人。他发表了若干篇成功的实验报告。
怀特对此加以肯定,同时还指出酒石具有清洗功能。他说,因为酒石对梗阻性疾病特别有效,“据我观察,可溶性酒石在医治因有害体液积聚于主要脉管而引起的躁狂症和忧郁症时,比医治因大脑缺陷引起的同种病症更为有效。”
关于其他溶解物,劳兰还列举了蜂蜜、烟囱灰、东方藏红花、木虱、龙虾钳螫粉以及粪石。
在体内溶解法和体外偏转术之间,我们发现还有一系列的实践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醋的各种用法。醋是一种酸,因此能消解梗阻,摧毁正在发酵中的异体。但在外用时,醋则是一种诱导剂,能把有害体液引到外表上。
这个时期的医疗思想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即不承认在这两种用法中有任何矛盾之处。尽管这两种用法中任何一种现在已无法用理性的推理来分析,但是由于设定了醋既有洗涤性又有诱导性,因此它便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起作用。
于是,它不需要任何媒介,仅仅通过两种自然因素的接触,便可起作用。因此,有人推荐用醋来擦洗剃光的头。《医学报》(Gazettedenddecine)引述了一个庸医的例子,该医生
“用最简单便当的方法医治了一批疯人。
他的秘诀是,在把病人上上下下清洗一番后,把他们的头和手浸在醋中,直至他们入睡后或更确切地说直至他们醒来后才停止。多数病人醒来时病已治愈。他还在病人剃光的头上敷上切碎的川续断类(Dipsacus)植物叶草。”
3.浸泡沫。
在这方面有两个观念起作用、一个是与涤罪新生的礼仪相联系的沐浴观念,另一个是更具有生理学意义的浸泡观念,即认为浸泡能改变液体和固体的基本性质。
尽管这两种观念起源各异,其阐述的层次不同,但是在18世纪末,它们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结合紧密,以致人们感受不到它们之间的对立。有关自然本性的含混观念成为使它们结合起来的因素。
由于水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液体,因此就属于自然中最纯洁的事物。人类能够给自然界的本质上的仁慈附加上各种可疑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并不能改变水对人的恩惠。
当文明、社会生活以及读小说和看戏引起的幻觉欲望造成了神经性病痛时,返回到清莹的水中就具有洗礼的意义;在清澈的冷水中,人就会恢复其最初的纯洁性。
但是,与此同时,水天然存在于一切物体的构成之中,能够恢复各物体的自身平衡。因此水是一个万能的生理调节者。卢梭的信徒梯索表达了上述所有的观念。他的想像力既具有道德意义,又具有医学意义。
他说:“大自然把水规定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独一无二的饮料。它使水具有溶解各种营养的能力。水很适合人的口味。因此选用一种清淡的新鲜凉水,就能强健和清洗内脏。希腊人和罗马人把水当作万应灵药。”
浸泡的做法在疯癫史上源远流长。
仅用埃皮达鲁斯(EPi-daurus)的澡堂就可证实这一点。各种凉水疗法在整个古代肯定十分普遍。如果我们相信奥雷利安努斯(CaelnisAure-lianus)的说法,那么以弗所的索拉努斯早已抗议对这种方法的滥用。
在中世纪,传统医治躁狂病人的方法是将其数次浸入水中,“直至他精疲力尽,归于平静。”
西尔维乌斯(FranciscusSylvius)曾建议用浸泡来医治忧郁症或躁狂症。18世纪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海耳蒙特(VanHelmont)突然发现了水疗效用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对水疗的再解释。
根据梅努来(Menuret)的说法,17世纪中期的这一发现纯属偶然事件所致。当时有一名戴着铁镣的疯人被一辆敞篷车押送到其它地方,但是他设法挣脱了铁镣,跳入湖中。他在拼命游泳时昏厥过去。
当他被救上岸时,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死了,但他却很快恢复了神志,并恢复了正常。以后,他“活了很长时间,再未疯癫过。”
据说,此次启发了海耳蒙特,他开始将疯癫病人统统投入海水或淡水中,“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要在病人无防备时将其投入水中,让他们长时间地泡在水中。人们不必担心有什么生命危险。”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
而以趣闻轶事的形式传达的一个信息则是确定的:从17世纪末起,水疗法成为或者说重新成为一种医治疯癫的主要方法。
杜布莱于法国大革命前夕发市《训示》,对他所认定的四种主要病状(狂暴、躁狂、忧郁和痴呆)都规定使用定期浸洗的方法,对前两种病状还增加冷水淋浴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切思早已建议:
“凡是需要强神益智的人”都应在家中设置浴室,每隔两三天或四天就浴洗一次,“如果他们没有浴室,那么就因地就宜,以某种方式在湖中或其他活水处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