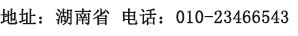“今川义元,讨取!”
“今川义元,讨取!”
“今川义元,讨取!”
胜利的呼喊,如同水滴坠落镜湖一般,那原本平滑如镜的水面,迅速扩散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不断远离,以至于整个湖面,都引点起了微微的波澜。
霎时间,今川义元阵亡的消息充斥着整个桶狭间。织田军闻讯,自然是大受鼓舞,奋勇杀敌,而今川军方面则是沮丧万分,姗姗来迟的今川家援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在主帅阵亡了之后,顿时变成了一帮乌合之众,不仅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反而作鸟兽散,朝着东边的骏河老家溃散而去。
很快,今川义元的首级被传递到了信长的手上,接受他的审视,而名刀“宗三左文字”,作为此次战役胜利的见证,,自然也被信长作为胜利品收入囊中,从此刀不离身,宗三左文字跟着信长东征西讨,直至本能寺的大火燃起……
“头,是好头!刀,也是好刀!”信长说,“这两者我都要了!传令下去,就地修建大墓,我要厚葬义元的首级,尸身即刻起派人送回骏河,而这把刀,我也要一直留于身旁。”
经历了紧张的厮杀之后,胜负已分,信长才终于开始审视战场。整个桶狭间一片狼藉,大雨瓢泼不止,却浇灭不了战场上弥漫着的硝烟,双方的死伤都非常严重,虽然义元的本阵人数偏少还遭遇到了突然袭击,但从死伤情况来看,织田家并不占巧,可见今川军战斗力之顽强。
只见这满山遍野的尸体,横七竖八、杂乱无章、枕籍相交,许多人因伤势严重、无法起身,只得倒在血泊中痛苦地哀鸣,无助地等待着死亡,就算有幸,从血泊中重新站起身来,但多半也会像藤吉郎的父亲一般下场。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史书上只会记述信长奇袭桶狭间的英勇事迹,后人们也只会看到信长霸业初始的辉煌无比,但光华之下,未见光明的地方,有的只是累累的白骨和数不清的血与泪。
我们肯定大人物对历史的引领,但更要尊重小人物对历史的奉献。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历史。
就在信长颇为得意的审视战场、巡视自己的胜利果实的时候,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前田利家!
只见他衣衫褴褛,破旧的衣裳上点点洒洒着斑驳的血渍,虽经历了大雨的洗礼,可是手中钢枪之上的血迹仍不见消退,足见其战斗之惨烈。此时的他,依靠在钢枪之上,浑身瘫软,满脸尽是疲惫之色。
“利家,你果然来了。”
信长朝着人群喊去,利家听闻声响,回过身来,顿时呆在原地,半晌回不了神。
“怎么?一年不见,就认不得我了?”
此时的利家,才终于反应过来,回道:
“主、主公……”
“嗯,这还差不多!”信长说,“好了,枪之又左,你回来吧!”
仿佛遭受了雷劈而被麻痹了一般,前田利家呆立原地,久久不能反应过来。自己的冲动之下杀死了爱知十阿弥之后就被信长驱逐,他没有怨恨,也没有放弃,而是日复一日的徘徊在清洲城下,不分严寒酷暑。
昨日夜半,在听说了信长独自离开清洲城奔赴前线的时候,前田利家抛下了还在熟睡着的妻儿,没有一句告别,不带一丝声响的就离开了,在他心中,对于信长的那份难以言喻的忠诚一直使他坚持到了今天。
现在,不懈的坚持终于获得了回报。
“是!”
前田利家的回应很是简单,但是旁人看不到的是,他眼睑的泪水,伴随着雨水在一起肆无忌惮的往下流。
前田利家,归位!
就在斩获今川义元的首级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之内,义元的主力部队两万五千人的骏河军,就好像受到了引力的牵扯一般,齐刷刷地向东方老家退去了。自知实力不足的信长,也没有组织追击,而是召集现场的织田家高层,召开了一场战后临时会议。
讨论的主题,当然是下一步的战略,毕竟在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还有八千人的三河军在等着他们。
当然,讨论归讨论,如此大胜,自然免不了一股吹捧溢美之词,这些马屁话,是点缀,更像是必须的开场语。
“恭喜主公!在您英明神武的带领之下,我们才会取得如此一场难以想象的胜利!”
“是啊!要不是信长殿下的果断坚决,纵使有着神灵的庇佑,也绝不可如此简单地取胜啊!”
“神灵?什么神灵,主公就是我们的神啊!”
信长静静地听着,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波澜,过了一会,才慢慢地问到:
“此间大胜,固然可喜,可是,又有谁知道此战我等为何取胜?”
见状,丹羽长秀回道:
“《孙子兵法·行军篇》有云‘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主公您看,这桶狭间山路崎岖狭窄,四周山峰群起,不就是兵法中的所说的‘天隙’,大军途径此地,应当速速离开,怎可就地安营扎寨。”
事不唯一,这点的确是取胜的原因,但绝不是全部。
“依我看,主公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今川义元貌似强大,实则如纸糊的老虎一般,外强中干。”
自从织田信行第一次叛乱失败之后,被信长释放了的柴田胜家,突然成了信长的“死忠粉”,不顾一切的支持信长的决定。
“此役的关键,在于我们悄无声息的接近了义元本阵却不被发现,而午后的这场疾雨,不得不说是重中之重,不仅掩藏了我军的行迹,还粉碎了今川军支援与撤退的道路,同时,风向是西北风,恰好迎合了我们进攻的方向,雨点直接打到今川军的脸上,使他们睁不开眼,却只落在我们背面,我们丝毫不受其影响。之前在热天神宫占卜之时,所有的铜板皆阳面朝上,这所有的一切,正是主公的‘天时’庇佑!”
众人听言,交口称赞,没想到平日里看起来性情粗暴、口无遮拦的柴田胜家,竟也有如此细腻之处。
“从此处放眼望去,皆是主公的‘地利’之便!大家看这桶狭山间,山不在高,有棱则灵。这些支离破碎的山峰余脉,犹如一个个棱角一般,如果大军平铺直入,则必将受到地势带来的阻碍,所以今川义元才会排列成一字长蛇之阵以求快速通过,而这,却给了我等奇袭之机。”
有理有据,环环入扣,看来柴田胜家对战局的把握,还是相当有能力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主公的带领之下万众一心。试问,除了主公、还有谁?能在不发一言一语的前提之下,就能引得尾张军民自发跟随奔赴前线。因为有主公在,我们“人和”的优势才会被如此充分的发挥出来不是?”
听了柴田胜家的话,众人纷纷称是,大伙都很聪明地懂得,无论何时,把功劳归于自己的领导,总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可惜,信长就是信长,并不难同常人而语。
“诸位言之有理,可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根本的原因,而无法探究到真正的原因,我们这次的胜利就只会是一次偶然,并不是真正的常胜之路。”
信长严肃地问到。
众人见状,也是哑口无言。
雨势渐渐地小了下去,虹销雨霁,彩彻云衢,光明重回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新鲜。
“主公,我想我知道了。”
言者,正是木下藤吉郎。
“各位大人分析之准确令我折服,但我觉得,此中有一处地方非常蹊跷。”
“何处?”
“就是在我们西边,我们来时的方向,盘踞着的八千三河军。要知道,昨日三河人就占领了大高城,今晨又攻下了五大寨,这样一来,等于将尾张的东线完全封锁住了。可以说,我们的行动完全处在三河人的监视之下,可他们为什么无动于衷呢?”
藤吉郎说,“还有,我们是在午后奇袭了桶狭间的,按照时间来算,三河军也应该抵达清洲城下才对,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清洲城的半点消息,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信长迫切的想要知道这隐藏在平静水底之下涌动的暗流到底是什么模样。
“据我推测,在我军离开清洲城不久,我们的行踪就已经被松平元康(德川家康)发现了,只是,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否则,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胜利了。我猜,他已经猜测到了我们的企图,故意放我们过去,坐观事态发展,义元胜,我方被全歼,他就顺势拿下清洲城,继续当好今川家的先锋军,但是,如果义元败,那么他就可以从今川家的控制之下独立出来!”
“这,你能确定?”
“当然!早年我游历四方,也得以亲眼见过松平元康和今川义元,据我所知,虽然三河国早已归属今川氏,但松平元康的复国之志却从未湮灭。此等复国良机,他怎能错过?”
“对!我也同意藤吉郎的看法。”
丹羽长秀说道:
“一千多年前,在那场决定中华归属的淝水之战中,前燕旧属慕容垂,在前秦溃败的时候,不是兴兵抵抗,而是重返故国,恢复前朝。现在,松平元康只是想做一件和当初慕容垂一样的事情罢了。”
“我懂了!”信长起身说道:
“传令下去,所属各部原路返回,沿途切忌与三河军发生冲突,那些失地也暂时不要去管,只需径直返回清洲城则可,有敢违令再起事端者,斩!”
王剑青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