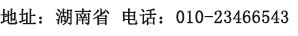讓詞學回到江南
——中國詞學會第八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總結
彭玉平
本屆詞學會已進入學術總結階段,意味著到尾聲了。按例曲終當奏“雅”,但今天能奏出什麼曲調,我實在是不敢說了。自受命為大會做學術總結,確實是誠惶誠恐,度過了一段食無味、寢不安的日子。剛才聽了幾位老師的分類總結,我覺得大會精義言之略盡,就好像“崔顥題詩在上頭”,我能說的就更有限了。但這幾天拜讀各位的大作,也確實給了我非常豐富的閱讀體會:有的讀得興會淋漓,有的讀得津津有味,也有的讀得半懂不懂。這種不同的閱讀感受與我本人的知識結構不平衡有著直接的關係。
本次會議收到論文篇(不包括自帶論文),內容幾乎涵蓋了詞學的所有問題。我的總結準備從五個方面展開:1.詞學本體論;2.詞史研究;3.詞的接受史;4.詞學文獻;5.詞學理論與批評。
在詞學本體論方面,有詞調、詞律、詞樂的研究,在句式結構方面有對領字的分析,在詞與其它文體的關係有詞與詩、詞與曲、詞與書、詞與小說等多方面的研究。
以詞人詞作為核心的詞史研究在本次會議中占了絕對份額。這其中既有概論性,也有專題性的研究,如詞的意象、時空觀、主題、風格、地域、典故、流派等,都有專門的研究。還有不少對詞人生平的考訂,成果相當豐碩。
在詞的接受方面,包括詞人接受、詞調接受、作品接受等,呈現出接受史的良好格局。
在詞學文獻方面,輯佚、版本、書劄、校勘、注本等均有涉及。
在詞學批評和理論方面,宋金元部分的文章雖然不多,但明清與民國還是甚多,這與這一時期的新文獻較多、學科格局還不穩定應該有直接的關係。
有這麼寬的覆蓋面,有這麼多深度的研究,可見本次詞學會確實有新的氣象。詞學回到江南,註定是一場回家之旅。我的家鄉雖然距離這裡只有一百多公里,但一直到今天,我才感受到“江南大學”這個名字的特殊魅力。
下面我想分領域談談我的粗淺體會,因為時間有限,閱讀不精,再加上我的領悟能力本身也很有限,所以我今天談到的文章,如果在方向上說錯了,請多多包涵。同時為了言說便捷,凡涉及作者名字,一律直呼其名,但敬意藏於心間,也請諸位諒解。
一、詞學本體論
1.詞調、詞律、詞樂
詞調及相關問題研究是本次會議值得注意的一個話題。
田玉琪的詞調研究已經高居學界一席,他為本次會議提交了一篇《詞調學研究的學術空間》的文章,希望能對詞調學在詞調的發生演變、運用、圖譜、音韻和音樂五個方面進行專題性的學科構建。我直覺在這個領域,田玉琪的眼界是值得信任的,很期待田玉琪的詞調學新著早日問世。
岳珍考察了早期詞調《麥秀兩歧》的源流變化,認為該調有多種異體流行,其中含有“大樑新翻”體,《教坊記》中的《麥秀兩歧》只是一般樂曲。作為詞調的《麥秀兩歧》的體式都是通過“摘遍度曲”的方式從教坊曲中生成而來。關於《麥秀兩歧》詞調的起源、體式問題,該文作了細緻的分析。這是僻調,考察也相對較難,但因為屬於早期詞調,實際上由此可以啟示勘察詞體起源的另外一種維度,文章也因此別具價值。
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二調,歷來有二說:有的認為是“百代詞曲之祖”;有的認為是託名之作。王衛星採取的方法是內證,經過細緻的比勘,她認為在字詞句篇以及由此形成的體勢、意象、意境、章法等方面,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二調與李白的《寄當塗趙少府炎》《灞陵行送別》、贈內即代內贈詩高度相似,以此來證明此二調應確為李白所在。類似這種雖然沒有新見資料,但從內在氣象的論證,有的時候更有力量的。
詞又名長短句,句式參差不齊是詞體區別於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徵。北宋前期是新詞調產生的高發期,同調異體突出,新生詞調在主導句型、句式組合、句法節奏等方面,都有不少新變,這些新變也是新的詞體審美觀念形成的基礎。姚逸超的文章對此有相當詳盡的分析。普義南通檢首夢窗詞中的單領字,對其疏通句組前後文,造成時空轉折、意義曾深的結構作用作了分析,因為從一個一個字的具體考量中分出作用類型,我相信他的結論是有力量的。
有來歷的風雅才是真風雅,詞為何也稱“琴趣”“琴趣外篇”?就是因為不少詞調乃是由琴曲轉變而來,這不僅有《琴調相思引》等帶有琴曲意味詞調的顯在特徵,也有從琴曲《醉翁吟》到詞調《醉翁操》等依琴曲創制詞調的軌跡可尋。很顯然琴曲是詞調的重要來源之一。高瑩《唐宋詞調與琴曲關係略論》一文在對若干琴曲與詞調關係分析的基礎上,對於詞的起源和特徵等也做了分析。
盛配似乎被關注的程度不高,但他的的聲調之學,以夏承燾、龍榆生的聲調之學為基礎,在四聲通變說,編訂四聲詞譜等方面頗多貢獻,雷淑葉的文章有發微之功。關於聲調之學,這次會議還有雷淑葉與施議對先生關於文章體制與聲調之學的對話,可以一併參看。
潘玲在年詞學會上提交的論文是對《西河》詞調的分析,但她沒到會。這次分析的是宋代方千里、陳允平和楊澤民三家和清真詞,她的論述角度側重在詞調,這次雖然只是考訂了《瑣窗寒》《花犯》兩個詞調,但她的計畫有28調,後續的規模研究更令人期待。她應該是可以與田玉琪進行“高端論壇”的不多的學者之一。
周韜對姜夔《霓裳中序第一》的聲律進行了新的考訂,認為與霓裳舊譜樂譜不同,姜夔特別在以平聲為上聲方面做了嘗試,一方面借鑒近體詩律,同時通過攤、減等方法構建偶言律句。這文章我讀得辛苦,但這不是周韜的問題,而是我本人對詞律問題一直心存畏懼所導致的。田玉琪對宋詞“入代平聲”說作了新的檢討,認為這種入代平聲雖然有,但是也屬於偶然的情況,並非必然的法則,入聲與平聲的區別仍是一直被強調著的。他對《詞林正韻》的批評比較犀利,認為頗多不符合宋詞實際。胡建次對民國時期詞學對詞律或尊或破或合的幾種觀念作了分階段分類型的分析。張春義、田玉琪從清商樂“依曲填詞”的特點考察其與詞體生成的關係。詞樂研究為大多數人視為畏途,這樣的文章除了學術價值,還特別需要學術勇氣。
宋詞演唱多協以樂器伴奏,而阮正是其中重要樂器之一種,其地位僅次於古琴,獨奏、伴奏、協奏皆可,兼具七弦琴的雅樂屬性與琵琶的俗樂特質。這意味著阮在宋詞演唱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我從董希平《阮與宋詞演唱》一文獲得了不少音樂學方面的知識,這是詞學中相對寂寞的一域,有待於詞學家與音樂學家共同的努力。
明詞怎麼唱?這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讀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就知道南宋就有很多詞無法唱了。但根據史料,明詞的自娛性歌唱仍在一定範圍內延續,歌唱形態發生了變化,詞人和童子成為歌唱主體。作者薛青濤列了一個長長的唱詞資料,讓你不信也得信明代唱詞的盛況。只是詞人與童子唱詞的專業水準,我不免有所懷疑。
2.詞與其它文體的關係
樂府曾是音樂機構的名稱,也是後來諸多韻文的代稱之一。在宋代,樂府一方面與詩文攜手而行,另外一方面也與小詞並稱,這種錯雜的情形背後有著怎樣的原因?黃賢忠從宋代32部詩話和12部詞話入手,詳細考量了樂府語義的內涵及其與詞體之間的離合關係,認為其中包含著文學復古情懷、詞體變革意識和對雅化的審美追求。
楊吉華從情與志的關係來看詞與詩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關係,雖是老話題,但說得更細緻了。李靜論述朱淑真“以詞為詩”,分析的文本是詩歌,但解釋的文體內質屬於詞。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宋代詩詞的交叉顯然不是單線的,至少是雙線的。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領軍人才,又是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詞也是與秦觀並稱“秦七黃九”,那麼黃庭堅的詩詞與書法會有怎樣的關聯呢?這是一個很有興味的問題,由興波的文章重點分析黃庭堅晚年在這三者之間的互補情況。文章不長,但值得一看。
賀鑄的詞集為什麼叫“東山寓聲樂府”?可能很多人沒有仔細想過,顏慶余的文章告訴我們,其實就是因為他以詞體來寫作樂府,所以帶有明顯的古樂府的風格,這個意思鍾振振也提出過賀鑄“以樂府為詞”的說法,顏慶餘把這個說法好像倒了過來,說是“以詞為樂府”。兩種說法的在什麼層面相合,在什麼地方相離?或許是另外一篇題目的文章了。
陳平、黃志浩對北宋遼西夏時期的民族交融與詞曲流變作了分析,側重在詞曲文體的部分合流上。左洪濤、孫許亞分析金代王喆道教詞對散曲的影響,重點分析在內容、體制形式上入散曲的情況,材料很豐富。左洪濤在道教詞這個地盤呆了很久了,他的研究也越來越有體系。
文體的互參是文體學中值得注意的現象,這種互參不僅在韻文或詩文內部為常,即便小說與詞也頗多文體關聯。宋人為加強詞的敘事功能,頗多融攝唐人小說之例。張振謙《論宋代以唐人小說入詞》就關注到這種文體現象。
二、詞史研究
以意象為中心考察詞史發展,自然是一個不錯的角度。
蟬不僅是詩詞的重要意象,也往往是被詠寫之物。高峰以唐宋時期的詠蟬詩詞為論述對象,分析了蟬的意象在襯托環境之清幽到彰顯詞人之清高再到轉寫亡國之悲情的變化,是一篇源流委具、意蘊層深的文章。嚴紀華對“莫愁”的文學意象為中心,考察了28首莫愁詞的情況,這種對宋詞主題意象的考察,可見創作流變的軌跡。
宋人頗多詠蘭詞,但所謂“蘭”應有分屬蘭科之蘭花與菊科之蘭草、澤蘭之別,此在宋人相關著述中已有較為清晰的辨析,蘭科與菊科的區別也帶來作品比德之差異,而宋人“詠蘭詞”若細加分辨,亦對此判然有別。王偉勇《宋人辨蘭花及所填詠蘭詞考述》是一篇頗見功力的文章,既具科學精神,又具審美判斷。我想像王偉勇在蘭花蘭草面前仔細端詳的樣子,那應該就是一種詞的姿態。
徐煉的文章題目叫《“昨夜”情結》,分析“昨夜”在詩詞中頻繁出現的現象及其原因,於不經意之處見出眼界和判斷。
時空觀不僅是哲學問題,也是詞學問題。本次會議有數篇及於這一話題。
宋詞中的“時間書寫”以對光陰易逝的焦慮和對生命永恆的渴望為主旋律,既珍重個人的現世時日而弱化政治和社會生活,也因“徹悟”而愈發清醒深刻,由此生發出諸多富有啟發性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智慧。以前說讀史使人明智,其實讀詞也一樣使人明智,關鍵是你能不能讀出來。宋秋敏的《宋詞“時間書寫”的文化蘊涵與審美心理考察》對此頗有發明。彭曙蓉對元末行旅避難詞中的時間詞語進行了“密碼破譯”,“密碼破譯”是她的原話,不是我的評述,確實時間書寫是考量作品的一個重要維度。
注重時間,當然也要注重空間。王曉驪《論唐宋詞空間建構的身份意義》從性別色彩和身份指向兩個維度分析了唐宋詞空間建構的軌跡及其彼此關係,頗見理論眼界。羅燕萍考察了宋代園林對詩人詞人心境和詩詞作品在文化場域、審美特徵、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張建偉、殷昆就專題分析元代詞人的地理分佈與群體特點,他們有很多地理分佈的資料,諸位可以看論文,他們把元代詞人的分佈格局與元代政治、軍事、版圖和民族政策結合起來,這樣的研究理路非常值得信任。
不用說,以詞人詞作詞集為中心的研究一定是詞史研究的主體
《花間集》似乎是個永恆的話題,本次會議有多篇文章涉及此集,或分析其色彩,或分析其題材、地域等。《花間集》中的詞雖然提供了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但以金、紅、綠為主色,且大多與女性有關,王慧剛由此認為《花間集》的這一特點,有可能直接促成“詞為豔科”觀念的形成。這個觀點不算新,但作者的分析非常細緻。黃海關注的則是《花間集》中的山水清音,他認為通過對其中的神話與地域描寫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詩歌在文體上對詞體的具體影響。“以詩為詞”不僅是後來拓寬詞境之需,也是詞體發展之初的一種基本事實。與黃海以《花間集》中的山水清音為論題不同,羅賢淑關注的雖然也是山水詞,但以整個唐五代一百餘首詞為考察範圍,不僅分別題材,也考量地域,並將其發展氛圍中唐、晚唐和五代三個時期,不同時期雖風貌有差異,但柔美的風格大體不變。
一調有一調之體式,也有一調之題材、主題方面的大致規定性,故由對一調源流的考察,也可見詞史發展的部分軌跡。《臨江仙》詞調是唐宋常用詞調之一,胡秋妍以唐五代時期37首同調詞為考察對象,揭示了雖同為“緣題所賦”,但依然有主題差異的演變過程。這樣的考察應該是有說服力的。
詞體雖在唐宋兩朝從確立到極盛,但其實經歷了從“唐音”到“宋調”的變化,這一變化的最終完成應該是在北宋後期。“唐音”情感豐盈,自然雅潤;“宋調”則意脈渾厚,富豔精工。這當然是從大概意義上區分的,實際上唐音與宋調的共存仍是長期的。付繼成以賀鑄、周邦彥為考察中心,梳理並分析了這一轉變的過程及宋調特徵的形成。
詞之唱和既可見一時之情誼,亦隱可見詞藝之較量,故唐宋時期,或同調次韻,或同調異韻;或彼此唱和,或自和己作,或身後追和,其唱和形態的豐富多樣已經與詩歌唱和等無二致。趙惠俊以唐宋詞體唱和的多元文本形態與唱和形態的擴容為研究對象,不僅勾勒出唱和的形態唱和,也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展現了詞體詩化的軌跡。
宋代文人地位相對尊崇,休閒心態也因此得以放大。張翠愛注意到這種身份和心態,故從休閒詞考察宋人的休閒文化心態。劉睿認為宋詞中部分關涉城市政治空間的作品,有將原本屬於精神空間的內容向外延伸的可能,這在貶謫詞、詠史懷古詞、邊塞詞、隱逸詞中表現較為明顯。這其實是用一種新的視角審視相關題材的作品,有一定發明。
以詞紀史是兩宋詞中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而且這是伴隨著“以賦為詞”“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以經論入詞”以及回憶性書寫等創作手法而不斷拓展的。換言之,這種致力於拓寬詞境的表現手法,潛在的動力就是能更充分、更靈動地“以史入詞”。這一類詞在抒發詞人一己之情懷的同時,也多有時代精神的折射。黃雅莉的文章對“以史入詞”創作現象及發展軌跡的探討,不僅系統,而且深入。
吳瓊《宋代“盛傳詞”芻議》通過對62首據說的盛傳詞的分析,得出宋代盛傳詞與宋詞經典名篇重合率極低,本質原因是文人審美與民間審美的離合問題。這其實也是宋代不少詞人備感困惑的問題,為什麼自己很自得的詞不為人欣賞,而自己其實不怎麼滿意的詞卻廣為流傳。其實這種困惑不僅宋代人就有,後來各朝人也都有,堪稱“江山代有困惑出”。這涉及到傳播學與經典學的離合關係,值得仔細研究。
宋代節日繁多,其中皇帝、皇后之生日謂之“聖節”。聖節例多詩詞,其內容也有大致的規定性,往往以聖誕應瑞及仁化構建帝王形象。余敏芳的文章即以此為題。
有一組關於柳永的文章,也許可以集中在一起說一說。
姚蓉對柳永都市詞的敘事模式做了探討,因為柳永的敘事結構以場景為中心,重點寫節慶及都市繁華。姚蓉說,讀了柳永的都市詞,很難說中國沒有狂歡節,很難說中國人沒有狂歡精神。我讀了姚蓉的文章,也有類似的體會,但我想這與柳永這個人比較自嗨也有一定的關係,狂歡也可以是一個人式的。王玫對柳永的“賦頌體詞”這一新的詞體形式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考量,認為一方面促進了詞體詩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轉換了詞體功能。
方穎對現存海甯唐氏寫本《屯田樂府》的文獻價值作了分析,這個本子最初由張文虎在毛晉汲古閣本的基礎上根據宋本《樂章集》校對後編成的本子,因為是寫本,知者不多,感謝方穎把這個本在重新帶進學術界。魏瑋對柳永是否觸犯宋仁宗以及拜見宰相晏殊一事是否屬實,進行了新的考辯,根據當時的考試與授官制度,以及“賢俊”一詞的使用習慣等,作者對這兩件事都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
薛瑞生是柳永研究的大專家,他光臨本次會議,為會議增大光輝。他對《鎮江府志》中收錄的柳永《墓誌銘》進行了側重在宋代官職方面的解讀,認為此《墓誌銘》應非偽作,並對柳永的若干仕履作了新的闡述。考辯文章而寫得文氣充足,我受益良多。
看來柳永不僅在他生活的時代備受寵倖,即便到了今天,也受到很多學者特別是女學者的高度關注,男神果然是男神,一紅就紅千年,這也算是柳永作為不倒的偶像的一個證明。
劉熙載說“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馮煦說歐陽修的詞“疏雋開子野,深婉開少遊”,歐陽修詞的深致受到了批評家的集體認同,郁玉英圍繞著“深致”二字對歐陽修詞的美學特質作了深度的開掘,認為歐陽修晚年和貶謫夷陵之後,創作的深致得到更多體現,我接受這個結論。
關於詞人身份的轉變,大體經歷了從詩客到詞人,從伶工到士大夫的轉變。神宗時代,文化昌明,在歐陽修之後,蘇軾堪稱一代文化之宗師。以蘇軾為中心,文士雅唱構成了主流,這與詞體功能“結人心,厚風俗”的轉變密切相關,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指出向上一路”。楊曉靄對這一時期文士群體的創作特徵作了細緻的辨析
北宋的莫襄墓碑有墓誌銘並序,碑陰也有五首《踏莎行》挽詞,張如安對此碑的文字進行了細緻的考量。在詞調創新逐漸成為趨勢的北宋前期,有一個人好像有意回避詞調的創新,這個人就是晏幾道,劉學的文章分析晏幾道詞調與詞心的關係,寫得很細緻。
劉尊明考量了在長達22年的時間中,蘇軾創制長調慢詞的情況,分階段探索其心境的變化以及時代的影響。李靜以“坡仙”為關鍵字,考察蘇軾詞的胸襟氣度與精神風韻,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角度。我曾經看過一篇介紹性的文章,說八歲的小東坡怎麼怎麼,其實最小的東坡也有43歲的。東坡有“仙氣”“仙味”,也應該從黃州說起的。沈松勤也關注到蘇軾的黃州詞,但他取的角度是對勘蘇軾在同時期寫的《蘇氏易傳》,這一對照就發現問題了,因為《蘇氏易傳》中強調的“性命自得”觀念,分明也是這一時期蘇軾詞的內在精神,如《蔔運算元》中的“幽人”其實就是一個“履道坦坦,幽人貞潔”的幽人,只有上升到這一高度的詞才能稱為“士大夫之詞”,文章寫得很有深度,很嚴肅,我覺得跟沈松勤給人的印象也是一致的,但其實沈松勤這人“即之也溫”的。
整個北宋,幾乎是江西人的半壁江山,政治上、軍事上、文學上,不少江西人擔任著扛鼎的重任。在文學上,以黃庭堅領銜的江西詩派實際上牢籠了南北眾多詩壇健將。詞壇的江西詞人群則是在南宋時期逐漸形成,他們對江西地域的認同構成群體創作的主要方向。王毅的文章多方面分析了這一問題。
宋末張炎《詞源》就曾經感歎“難莫難於壽詞”,因為寫來寫去不過富貴、功名、神仙三者。雖然北宋的晏殊就開始寫作自壽詞,並有26首之多,但未在周圍形成大的風氣。到了南宋,自壽詞的創作就蔚成風氣了,其中也頗有佳作,這與南宋的祝壽風氣有關,當然也與詞體功能的轉變有關。張文利以南宋自壽詞為論述對象,我認為結合了時代、個人、文體來分析,確多中肯之論。
諸葛憶兵這次的文章是對劉辰翁的豔情詞進行專題分析,雖然作品只有12首,但有部分作品把豔情改造成書寫亡國之音的載體,這個變化有點大。但周濟也說過,豔情有的時候只是面子,裡子可能是多種內容,把身世之感打併入豔情,也曾經是不少人的嘗試。諸葛又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劉辰翁個案,這屬於宋代豔情詞的典型變調了。
關於辛棄疾與張鎡的唱和詞,我此前沒關注到,尤其是在這種唱和之中究竟有怎樣的隱秘心境,是一個繞有意味的話題。這次有位作者因為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和作品,所以提交了一篇專題文章,他的名字叫“劉方”。鄭慧霞對辛棄疾《清平樂?村居》的聲景書寫展開研究,細緻可讀。齊凱認為對辛棄疾《青玉案?元夕》主旨的解讀呈現出過度闡釋的傾向,他的結論是此詞不過寫傳統的男女情事,這個結論前人也有類似的說法,但齊凱用細緻的分析佐證了這個說法。趙曉嵐追源溯流,分析了西漢賈誼、司馬相如、揚雄對辛棄疾性格、思想和創作的影響。這對於深度瞭解辛棄疾其人其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資源。
朱惠國等分析戴復古《石屏詞》的用調特色,簡單來說,有因襲有創調有創體,他的創調創體影響不算大,但在南宋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黃敏對姜夔詞的用調與詞風關係進行了分析,認為姜夔詞風在韻部的選擇、句度的組織和聲律的安排等多方面非常用心,他清勁峭拔的聲情特點與其清空騷雅的詞風是有著直接的關聯的。從詞調角度介入詞人詞作的研究,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維度。
典故是詩詞中的“常客”,因為典故可以帶來詩詞的婉轉之意,拓寬詞旨詞境。本次會議有兩篇文章重點論述典故問題。相比較而言,北宋詞之用典多取自詩文,而南宋詞則採擇于經史子集之中,且多僻典,一些詩詞大家如陶潛、李白、蘇軾等也作為人物典故出現在詞中。陳麗麗《論南宋詞用典及詞風之變》用力即在這種變化上,她尤其注意到這種用典的變化實際上帶來了更深程度的文人化與雅化傾向,這個結論我認為是穩健的。張梅、邱忠善對辛棄疾詞中“典故類聚”的敘事話語進行了頗為全面的分析,典故使用的得與失從來都是相對,因為使用典故的意義從來都是有選擇性的。批評的人往往用被棄置的典故內涵來指責使用的不精准,讚賞的人往往在典故與作品語境中的契合中感到一種特別的韻味。但“典故類聚”其實是危險的,不是高手,儘量不要嘗試,辛棄疾當然是高手,他應該屬於例外。我最近讀況周頤批點陳蒙庵填詞月課,陳蒙庵填了一闋《瑣窗寒?金風》,況周頤讀了初稿,說你只是寫了秋風,沒有說“金風”,這個“金”字要刻畫出來,所以況周頤的修改稿用了一系列關於“金”的典故,如金縷衣、一鉤金、金波等等,我感覺就是強調“典故類聚”的方法,但這樣對初學填詞的人真的好嗎?至少我是懷疑的。
很多詞有“本事”,但本事的是與非,卻是一個不易說清的話題。本次會議有三篇文章與此相關,且彼此意見頗有不同之處。
我們讀唐圭璋先生的《詞話叢編》,第一部便是楊繪的《時賢本事曲子集》,宋代的幾部詞話,也大多以敘述本事為主,清代葉申薌也有一部《本事詞》,把詞後面的本事記錄下來,成為古代詞話的一項基本內容。我也讀過以詞的本事為主題的博士論文,但這次會議,關於這話題就有不同的聲音了。
宋學達並不否認詞本事的文獻學價值,但他經過對陶轂的《風光好》、周邦彥的《瑞鶴仙》與蘇軾的《蔔運算元》三詞的源流分析,認為其中存在著嚴重的虛構現象。宋學達為此提出了新的“兩個凡是”的觀點:“凡有大量細節描寫者、凡以詞句比附情結者,皆應懷疑。”這“兩個凡是”說得是否重了一點?最好請王兆鵬與劉勇剛來回答。
劉勇剛的文章題目就叫《秦少遊的鵲橋仙為誰而歌》,他的結論是:這首詞的本事好多,拿一件來說,即便不是寫給小師母王朝雲,也是寫給長沙義倡的,創作地點是郴州,時間是紹聖四年的七夕。
王兆鵬與肖鵬繼續擔當詞學員警的職責,他們連袂考訂賀鑄的情事,根據賀鑄友人李之儀《題賀方回詞》提供的線索,終於解開《青玉案》隱秘情事。此詞是書寫真實的愛情故事,建中靖國元年()賀鑄寓居蘇州,偶遇吳女,一見鍾情。然因自身長相奇醜,加之仕途不順,自卑感強,每到社交場合就膽怯拘謹。愛妻去世後,更是垢面蓬首,不接世故。因而直到吳女去世,他也不敢向吳女表白,釀成無法挽回的愛情悲劇。《青玉案》和《感皇恩》便是歌詠這場愛情悲劇的姊妹篇。
從他們的考訂也提醒當代的詞人,不要以為把一段不想直說的感情寫在詞裡面就很安全,一旦遇到像王兆鵬這樣心明眼亮的“員警”,也許總有昭然大白的一天。同時也提醒知情者寫序或者題詞,筆下的文字要收一收,以免誤了兄弟的好事。
王兆鵬、劉勇剛兩人的大作,我一時覺得不好評了,我想偷個懶,把這兩篇文章交給宋學達來評議,也許是最合適的。
路成文從奇氣、理趣、巧思三個方面對蔣捷的《竹山詞》做了新的探討,尤其是注意到蔣捷素以儒者自視,說自己“平生著述,一以義理為主”,如此蔣捷詞的“理趣”確實有一個穩健的落腳點。
邵大為《潘閬行年系地譜》比較詳細地勾勒了潘閬的仕履及作品編年、系地,這類系譜為之不易,有時一時一地一事之考訂費時數年難得確證,為更精深的研究提供了知人論世之資。我對這一類文字滿懷著敬意。關飛考述了高觀國與史達祖的生卒年及其交遊情況,作品內證與外證結合,梳理論證清晰。
孫虹的箋注之學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由箋注而來的史實考訂也往往令人信服。這次她考證張炎北遊之事,結合宋元史料,提出了兩度北遊說,並對相關行程和作品作了分析說明,同時由兩度北遊說,也可糾正對張炎人格長期以來形成的誤判。這樣的考證小中見大,具有一定的範式意義。這次會議我們在許多場合都看到孫虹忙碌的身影,她對本次會議確實厥功甚偉。
郭勇對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的三個版本進行比較研究,得出最可採信的版本並分析其審美價值。知名度高的作品往往透明度低,郭勇的文章應該再次印證了這一說法的合理性。何麗娜分析沈周率性天真的小詞,注意其詞學觀與填詞創作的關係。
葉曄把視野放在明代,考察明代北方的填詞圖景,注意區域的組合以及不同區域之間的關係,同時對北方之詞如何與詩歌戲劇的融合作了分析。為詞史上提供了比較鮮明的北方品質。這篇文章站位高、視線遠而落地穩,我個人讀來很受啟發。
黃曉丹結合清初政治壓力、文體彈性與個人生命三者的關係來考察詞史關係和詞史觀念的建構,帶著明顯的以詞補史、存史的理想。這篇文章頗見格局,出自青年學者之手,值得鼓勵。我此前參加過香港浸會大學張宏生教授指導的一篇博士論文的答辯,論題與此相似,兩文若加對勘,相信各見風致。
劉東海從《全清詞》的分卷中整理順康雍乾四朝的題畫詞首,從中再選擇大型同畫題詞唱和詞為中心,探討其主題的流變,是一篇下了不少功夫的文章。鄧妙慈分析龔鼎孳和韻詞的詞史價值,作者不僅對此有分類分析,更認為這些和韻詞對清詞中興有直接的推動意義,也是一個不錯的角度。
清代的女性詞漸成規模,詞藝也日高,本次會議有一組關於女性詞的文章值得關注。
趙宣竹對順康時期的女性詞的藝術進行了專題研究,揭示他們既有師承也有創新的藝術特徵。同樣研究順康女詞人群體的還有陸佳慧、張祝平二位,他們合作對這一時期女詞人的選調、創調情況作了分析,勾勒了詞壇女性審美意識的確立過程。韓榮榮則對女詞人沈彩的《采香詞》做了比較全面的分析。韓紹平對清代女詞人楊芸的《琴清閣詞》中的酬贈、題畫詞做了分析。伏濤分析了顧太清的饋贈致謝詩詞,認為是“禮尚往來”的最佳樣本。這個結論很有吸引力。錢斐仲兼有女畫家、女詞人的雙重身份,陶運清、劉淩雲研究其詞中的圖畫書寫,可謂因人而論。徐燕婷對民國時期學者型女詞人的代表陳家慶做了深入分析,著重突出以陳家慶為代表的女性詞人已經在主流詞史中獲得與男性詞人並重的地位。
孫豔紅有個課題是“滿族詞體演變史”,這次她提交的成果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對承齡詞境的分析,認為他超越各派而獨有特色。納蘭可能是清代詞人中在民間接受度最高的詞人,塗意敏對《飲水詞》中的易代之思做了分析,這是對納蘭廣為人知的愛情詞之外,另外一種主題的開掘,頗有意義。
康熙時期梁溪詞壇有詞社,有家族詞人群,他們既創作,也編選本、刊刻詞集,形成了一個頗為蓬勃的詞學生態,這是任翌文章的主要內容。林宏達注意到清代張玉榖在雍乾朝有不少論詞長短句,這當然可見他的詞學觀念,但林宏達把文章的主體放在這一觀念之下家族詞人群的填詞概況,落實到創作的層面,一方面印證其詞學思想,一方面展現創作的風貌。
劉軍政《論劉榛的清樸詞風》認為:劉榛的詞,借稼軒風的形貌,傳遞理學的精神,表現出“清樸”的創作特點。劉榛此前並不大受關注,但從詞史研究而言,只有更多有成就的詞人詞作納入到研究的範圍中來,才能豐滿詞史的流變和格局。
藍士英考論趙懷玉與張惠言的交遊,事實的考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此而呈現出常州派既有鬆散的聯繫,也有未必清晰的傳承。這有點像我理解中的常州人的性格:在鬆散的群體中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陸有富對譚獻《復堂詞》如何體現“意澀”的技巧和“柔厚”的主張做了重點分析,也同時指出了其創作的若干不足之處。趙瑞華以“詞史”觀念為核心,分析了晚清詞創作是如何與此觀念進行實踐與疏離的。沈家莊、朱存虹對王鵬運及其詞和詞學活動、詞集情況進行了綜合分析。朱存紅還提交一篇關於王鵬運學詞道路的文章,可以一併參看。楊柏嶺的詞學研究兼重文獻和理論。這次他分析王國維詞的哲理意味,這個話題不算新,但他把握了王國維“多情”與“善思”兩點,理路是精准的。
美國的艾朗諾認為把李清照的每一首詞當做自傳是一種危險的行為,有可能導致一種嚴重的誤讀,他的基本理由是“男子而作閨音”是中國的創作傳統,今傳署名李清照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偽作。但喻宇明認為晚清閨秀鄭蘭孫的詩詞稿《蓮因室詩詞集》,富含大量自傳性書寫,具體來說是“不平則鳴”“感知慨事”,這兩個動力促成了終其一生的自傳性書寫。我讀來是認同的。因為我深深知道,“男子而作閨音”固然是一種傳統,而缺乏充分社會交流的女性,應該秉承的是另外一種創作傳統。
鍾錦對謝玉岑的詞進行了專題分析,著重揭示其因為英年早逝而帶來其詞展現了多方面的美學特徵,似乎無所特色,但其實謝玉岑也有自己一定的新創,文章對此有分析。謝建紅的《江南詞人——謝玉岑論》,也是專題討論謝玉岑的詞,謝建紅是謝玉岑先生之孫,他眼中的祖父肯定是別具神采的。這兩篇文章可以合看。
歐陽明亮對民國詞學教授周岸登的詞進行了專題分析,一方面揭示其自號“二窗詞客”背後對吳文英、周密的追隨,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其受到蘇辛影響的痕跡。管琴根據《天風閣學詞日記》梳理了夏承燾與馬一浮的一段跨越二十多年交往的記錄。主要揭示了他們的詩詞交往,為考察當時的詞學生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角度。許菊芳分析了劉永濟《誦帚詞集》中的餘首詞,注重其心史與詞史的雙重展現。
金春媛對張伯駒以“詩詞記戲”的作品和特點,張伯駒之所以能體現出這一特點,與他兼好詩詞曲多種文體有關。我最近關注梅蘭芳在民國年間的南北演出記載,當時風靡南北的情況,現在讀著也很震驚。張伯駒用詩詞來記寫曲壇,應該也有著類似的背景。餘意對民國時期北京的聊園詞社做了專題考論,這個詞社因為無社集行世,考論為難。但餘意參諸社員詞集以及其它零散的文字記載,勾勒出詞社的構成、社集和基本性質。
劉威志對趙尊嶽客港時期的《南雲詞》作了專題分析,這個時候況周頤、朱祖謀兩位老師已經去世,時代又有新變,所以這本詞集體現了趙尊嶽詞風的部分變化。汪中的籍貫是安徽桐城,但年後遷台,年去世。林佳蓉對這樣一位當代詞人做了詞作輯佚和析論,這是最近的詞史,也是最鮮活的詞史。汪超關注到10-19世紀朝鮮半島詞人對中國地名運用的情況,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視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為當代的文化自信添一重證據。
三、詞的接受研究
譚新紅以文學史為考察視角,對百年來詞體文學經典的過程作了勾勒分析,這是經典化的一個特殊範圍,有點類似於集體認同,其但影響力也因此非同尋常。顧寶林以清初為基本考察範圍,對歐陽修《漁家傲》十二月鼓子詞的擬仿和接受作了梳理和分析。
李清照的詞接受史已經受到過一定程度的關注,但如果說誰是第一讀者,可能答案還是很多,楊雨、劉曉麗給出的答案應該是王灼。王灼雖然不是最早評說易安詞的人,但他對易安詞的評價卻是奠基性和方向性,大致引導了此後對易安詞認知的基本定位。文章對南宋及明清學者群體的觀點作了梳理,認為他們與王灼觀點確實存在著呼應。我認同這樣的考察維度。
橘千早考察了蘇軾與柳永相同的22種詞調,相關的變化肯定有,更值得注意的與柳永完全一致的作品,可以看出蘇軾不是按照樂曲,而是參照柳永歌詞本身來創作的。直接一點說,柳永的詞因為得到蘇軾的敬重而逐漸成為範式。詞學史上經常津津樂道蘇軾說“我詞比柳七如何”的話,以為他一定要與柳永比出高低,其實英雄從來惜英雄,骨子裡的敬重也許是更根本的。
錢錫生從藝術接受的角度梳理了辛棄疾對後來詞人的影響,譬如語彙、意象、成句、句意、句式等,非常細緻。姜夔的自度曲不僅是在基本體式上影響到後世,而且在詞牌、詞序、正文三位一體影響後來,清代浙西詞派大力標舉,尤其好追和其自度曲,所以姜夔的這類詞也因此慢慢走向經典化。當然浙西詞派在模擬中也有變化。
李春麗的論文題目是《詞學史上的金元詞論》梳理了金元詞在金元明清和民國時期的接受史,包括對金元詞的文獻整理、對金元詞特質的認識以及金元詞與詞學史的關聯,有材料,有眼界,有判斷。
林淑華分析宋翔鳳對姜夔的接受,結合宋翔鳳的論詞絕句、論詞長短句,認為宋翔鳳對姜夔的接受主要體現在注重其詞中的家國之歎、詞史地位、工於音律等。王天覺分析辛棄疾在民國的接受,但他的視角落在民國時期的報刊上,對這一時期的辛棄疾就接受的新變與意義作了具體的分析。白帥敏專文考察范成大詞的傳播與接受,涉及版本變化、單篇傳播以及對其它詞人的影響。徐利華、馬興祥分析了《拋球樂》詞調在朝鮮王朝的受容和演變,這是域外詞學接受史,值得關注。
四、詞學文獻
作為第一部文人詞集,《花間集》歷來備受關注,但其校勘也自來問題頗多,李一氓的《花間集校》固為一時之精校本,但在文字、格律、詞意、名物等方面尚多遺留問題,馬裡揚的《〈花間集〉校議》列舉了大量事例,他的“議”也因此有了比較紮實的基礎。
唐圭璋先生以一人之力而編《全宋詞》,不僅令人感佩,更有力推動了20世紀至今詞學研究的發展。《全宋詞》雖續有修訂,但在劉榮平看來,依然存在著不全、失真、欠善、欠精之處,而在今人詞體韻律觀念、總集編訂經驗、文獻取資便利的情況下,已經具備了重編《全宋詞》的可能。劉榮平文獻功夫上佳,他曾以多年之力編纂《全閩詞》,當備嘗總集編纂之甘苦,也能深度理解和把握總集編纂的路數,相信他的建議是有建設性的。
張炎,不是那個寫《詞源》的張炎,據各類文獻輯補《全清詞》(順康—雍乾)卷漏收詞首,我直接在這裡表示敬意,找出這麼多,真是辛苦了。詹千慧對藏於上海圖書館之王鵬運的稿本《梁苑集》做了細緻的校讀,以看出其光緒九年()癸未秋前往開封省兄,至次年十月服闋入都以前的經歷和心境。羅慧、孫沁在受到饒宗頤先生指點的啟發下,細緻考察了寧波天一閣藏明刊本《淮海句式長短句》的情況,像這樣的私刻本,往往不大受關注,但其中也包含了值得關注的詞學思想。尤其是序言是草書寫的,要辨認清楚真是不容易。
鄭煒明、陳玉瑩有一個關於賀鑄詞版本、校勘、詞調等研究的系列計畫,這次他們提交的論文是以毛氏汲古閣未刻詞本《東山詞》為中心的源流考察。我對鄭煒明的文獻功夫是敬佩的。與發現新文獻相比,對新文獻的精准考訂才是更重要的。這兩年我也經常翻看他的《況周頤先生年譜》以及關於況周頤的兩本論文集,覺得他搜羅文獻當然勤奮,考訂的功夫也是非常厲害,這多少得益于饒宗頤、羅忼烈等先生的指導。
艾朗諾對今存李清照詞的真偽有很大的疑問,這個疑問當然有著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說“越是晚出的易安詞就越不可信”這個判斷很可能是有問題的,為此他把《花草粹編》中增補的九首易安詞歸為最不可信的一類。江弱水考訂了《花草粹編》中新增的兩首《攤破浣溪沙》和一首《減字木蘭花》,認為它們具備了不少專屬李清照的元素,說這三首詞是偽作,應該是欠缺充分證據的。江弱水的藝術直覺相當敏銳,但如果能輔以更多的直接證據,文章就更穩健了。我暫時選擇相信江弱水,因為今天艾朗諾也不在。
鄧子勉在詞學文獻搜羅和研究上,都是非常出色的,詞學界沒有使用過他整理的文獻的人應該不多,這次他考訂南宋黃公度的詞集文獻,依舊是一如既往的翔實清晰。劉尚榮整理校正了《東坡詞》的傅幹注,這是第一部蘇詞箋注本,這個本子曾經引起過龍榆生等人的注意,但傅幹《注坡詞》的價值遠沒有被充分利用,這個新本子相信能推動蘇軾詞研究的新發展。
鄒靜慧考察了公私書目中的《竹山詞》版本,將八種傳本分為兩個系統。楊景龍曾經做過《蔣捷詞校注》,中華書局年版,他要來參會,可以與鄒靜慧來進行對話了。周明初對從明清宗譜中收錄的若干明詞進行了考辯,一個基本的現像是假託明詞的現象比較突出,這為考訂文獻的時代歸屬、作者歸屬設置了障礙,周明初的文章雖只是舉例,但其實是為考訂真偽展現了考辯的範式,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張海濤考訂陳廷焯三種詩詞學著述《騷壇精選錄》《詞則》《杜詩選》,或考訂成書時間,或考訂鈔本情況,或考訂真偽情況。《騷壇精選錄》撰於陳廷焯早年,這是肯定的。我是在陳廷焯的孫子把這本書送我拍攝後,才瞭解到這本書的情況,後來還特地編了一本《白雨齋詩話》,以回報陳廷焯之孫對我的信任。這其中《杜詩選》我沒見過,張海濤好像也沒見過,但他提示了文獻線索,不管真偽,只要還存於天地之間,總是一件幸事。
薛玉坤的文獻考訂一直受到不少人的關注和推崇,這與他一貫的博學和敏銳是有直接的關係的。這次他以吳昌綬的相關書劄為核心,對近代詞學文獻整理工作做了多方面事實上的厘清。其中對我文章中提到吳昌綬與王國維交遊時任職何處以及吳昌綬編纂《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是否受到羅振玉督促的辨析,我完全接受他的結論,這與我讀書不廣、思考不精有關,在此謝謝薛玉坤的指正。小書修訂時一定據以改正,並說明來源。
許淑惠以陶湘撰寫的宋代詞集題跋22篇為對象,分析陶湘在藏書、校書等方面的心境,側重其在詞學文獻學上的地位。陳雪軍從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趙鳳昌藏劄》中擇出邵瑞彭致趙尊嶽的手劄25通,一一考訂其內容,相信他的考訂對相關詞學活動、詞學觀念有大的幫助。和西林在近代詞學文獻的發掘上頗有貢獻,這次他對新發現孫人和的《詞學通論》的版本、與吳梅《詞學通論》的關係、批語之價值、詞學之價值,作了相當全面的評述。蔡世平的《南園詞話》凡37則、《續南園詞話》26則,所述以理論為主,以白話撰成,讀來別有一番滋味。
五、詞學批評與詞學理論
詞一直被視為宋一代之文學,但那是從宋初五十年之後才開始的。為何在中唐“才子”催促詞體的產生、晚唐五代的“浪子”促進詞體的成熟後,會有這宋初五十年詞壇的沉寂。原因當然與宋初大力整頓士風有關。從宋真宗朝開始,國家元氣漸增,士子遊宴之風再起,詞體因而再度得到發展的空間。按當初的情況,似乎士子“浪”則詞活,不“浪”則詞死。其間因緣,頗多可深入思考者。張再林的文章便大體由此展開分析宋初詞壇沉寂的原因。
韓立平對宋代文學批評中的詩詞互證與辨體思想進行了分析,涉及文本校勘、本事探索、作者辨正、生平考訂等多方面的內容,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度。學術研究,有時換一種思維和角度,很快就能呈現出不同一般的現象。
哀怨之情是文學中的常見主題,也帶來特殊的審美傾向。宋詞中的哀怨也必然帶來宋代詞論中對哀怨的審美追求,潘筱蒨的文章探討的正是這一問題。
今存宋人詞選多有詞題,雖然歷史上頗有“詩有題詩亡,詞有題詞亡”之說,但此說其實存在著明顯的不合理性。現存詞題雖多為編者代擬,難免有片面性,但因為詞調的意義功能客觀上存在著缺失的現象,所以編者擬題也就因此有了提示閱讀和類型批評的功能。薛泉的文章對宋人詞選詞題的分析,我認為總體上是合理的。
相較後人擬題,宋詞小序則為作者筆墨,類似法國熱拉爾?熱奈特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副文本”概念。詞序多補敘詞事、還原現場,作者身份便也因此由隱以至顯,作品的意義建構也更為豐富,並有了大致的意義邊界與方向感。張曉甯《“副文本”視角下的宋詞小序》對此有比較詳細的分析。
張仲謀是明詞和明代詞學研究的祭酒,他這次提交的依然是關於明代詞學的論文,論述王世貞《藝苑卮言》的詞學史意義,著眼創作、選本和詞論的多重影響,小題大做,但做的有格局有氣度。岳淑珍繼續在明代詞學領域耕耘,這次她分析明代詞體正變論,她不是就詞學論詞學,而是結合明代詩學的正變觀來分析,這是建立在明代詩詞邊界比較模糊的基礎上,正變的問題,宋人雖已有一定認識,但明代才基本定型。
朱德慈兼有文獻與理論之長,在這兩方面都給學術界貢獻過厚重的著作。這次他從家族、姻族與清代詞派的關係切入分析,涉及諸多詞派背後的家族、姻族因素,展現了詞派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淵源。陳水雲探討的問題是明末清初詞壇的“求工”與“尚法”之間的關係。作詞難是這一時期不少人共識,陳水雲結合流派理論進行分析,彰顯了這一時代背景之下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孫克強從事清代詞學研究數十年,著作等身,其中付出的艱辛在在可見可感。這次他從詞學主張的系統性、詞選的影響力、創作成就以及與康熙朝官方思想,分析浙西詞派能夠主盟詞壇是多方面原因的合成。文章兼顧全面,持論平允。
昝聖騫認為常州詞派的聲律觀念主要導源於《樂記》中的聲學思想並形成自己新的內涵和體系,文章追源溯流,有一定的啟發性。梁雅英對王昶《國朝詞雅序》的異文與《國朝詞綜序》的關係作了分析,她從中發現了王昶對汪森、厲鶚詞學觀念的繼承與修正。文章中有字體比較和序文分合圖,應該是一篇很用心的文章。
譚獻是清末詞論的代表性人物,他借助詩學來推尊詞體,但又注意保持詞體的獨立性,其理論呈現出比較糾葛的狀況,高明祥的論文對此有比較清晰的分析。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國朝詞綜補》影響頗大,但對其人其書的研究還是比較滯後,閔定慶考述其家世和生平,為對其詞學和選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杜慶英則對譚獻在《篋中詞》中的點評與碑學的關係作了分析,她重點關注的是碑學、書學概念在詞學中的滲透。
我是溧陽人,溧陽屬於常州,常州詞派是詞史上影響最大的詞派,但我基本上沒有研究本土詞派,而是花了多年時間去研究隔壁浙江海甯的王國維。現在終於有人研究清末民初的浙江詞人如何在詞學上向常州詞派進行靠攏和學習,這使我內心也得到一種平衡。傅宇斌的這篇文章我因此讀著十分暢快。
楊傳慶從近代以來的書劄中分析詞學觀念的變化,這個資料來源很可靠,所以我想從中演繹出來的詞學也應該很真實。王平從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中提煉其尊體理論,認為俞陛雲在文體功能和藝術論上完成了詩詞同尊同工的地位。
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以論詩歌為主,但其中也有不少跨界的批評,其中有十則涉及清末民初的樂歌批評,這種新音樂文學批評反映了在新舊時代之際對樂歌文體的基本態度和觀念。如果民國也有大晟府,這種樂歌很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文體樣式,可惜民間行為終究導致了發展的緩慢甚至歸於沉寂。反省這一段歷史,體制的重要性便彰顯了出來。這是劉興暉文章的主要內容。
劉少坤、張寒濤把王國維的“人間”“境界”等概念放在王國維的生平學養和時代環境中去探討。他們認為“人間”一詞內蘊著王國維的宗教情懷,而“境界”一詞應該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第一點我持保留意見,因為王國維其實不精於宗教;第二點涉及到中西權重的問題,如果能在源流和權重上有更精細的研究,是我更期待的。
我自己的文章分析王國維與況周頤詞學觀念的相通,其實是對王水照先生文章的補充。王國維與況周頤各因所需,而提出自己的理論,但當剝開外緣,觸及到詞體根本的時候,兩人其實是合流的。我用的文獻來自《歷代詞人考略》的較多,因為這個文獻,況周頤是托劉承幹的名義來寫,所以不用違心地樹旗幟、帶帽子,更能真實地反映況周頤的真實心態。
《燃脂餘韻》是王蘊章發表在《小說月報》等報刊上的女性詩詞話,一方面保存了不少女性作品,另一方面要求恢復婦德觀念,總體上比較守舊。但在一個新的時期的守舊,其實也是一種批評的姿態。關於這本著作及其主要內容,可以參見習婷的文章。汪素琴專題討論了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的論說方法與特點,現代詞論也理當進入詞學史的範圍。
關於二十世紀詞學傳人的分代,施議對是開風氣者,倪春軍以第三代詞學傳人為中心分析晚清民國的詞學教育,這個選題很有意思,可見詞學傳承在方法和觀念上的若干新變。周于飛從施議對編纂的《當代詞綜》總結其“大當代”的詞學觀。我與施先生交往超過20年,深知他是一個有魄力、有眼界、有使命感和方向感的學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施先生會作為一種現象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
曹辛華目前的研究有從近代向當代發展的趨勢,證明之一便是他這次提交的《論當代詩詞批評史的發展、建構與意義》,這是一個新的領域,他對此已經有了一定的思考,相信他的思考會給大家帶來啟示。
劉宏輝關注域外詞學,提出了關於日本詞學史的建構及其意義的話題。關於日本的填詞發展史已經有專書問世,一本日本詞學史顯然也是學術界期待的。
鄭易焜對《國朝常州詞錄》的編纂及其詞學思想,突出了繆荃孫詞學交遊、創作觀念、詞學思想在其中的滲透。郭時羽對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三十年代初印本與五十年代修訂本作了細緻的比較,揭示不同版本變化所呈現出來的不同學術意義。譬如為什麼初印本選夢窗詞多達38首,而修訂本只選了10首,這種變化大有講究。龍榆生的這個選本影響非常大,但排序和選目也發生過很大的變化,這背後的時代因素不能忽略。
我前後花了一個多星期閱讀諸位的論文,這一方面對我是一種學術上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也為我有欠完整的知識結構進行有益補闕。我原來覺得學術總結是苦差事,但今天我不這樣認為了,因為收穫的快樂遠過於閱讀的辛苦。
但讀後我還有一些想法,也在這裡與諸位交流一下:
1.學術研究的本質是揭示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如果經過你的分析,這個對象沒有特殊價值,則相應的研究也就變得可有可無了。所以敘述類、概述類的文章除了編寫教材,建議儘量少寫,如果習慣了這種作文模式,很可能會習慣不創新了。而學術一旦無視創新,學術的生命也就危在旦夕了。本次會議帶有概述性質的文章數量不少,或許是應會急就之章。
2.謹慎介入一些關注比較多的領域,儘量避免選題的重複。除了有新材料,或者新理解,或者有新方法,否則相關的研究可能會流於重複與平庸。對一個多人關注的領域的介入,其實對研究者的學養會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聖歎批點《水滸傳》,提出了著名的“犯之而後避之”的理論,應該給我們很大的啟發。“犯”之後怎麼“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需要首先思考的問題,本次會議不少論文勇於“犯”,但似乎未能巧於“避”了。
3.關於文獻與理論的結合,劉熙載早就說過:“讀義理書要推出事實來,讀事實書要推出義理來。”事實與義理的結合註定是學術研究的正道與大道。我感覺有不少文章對事實的考訂固然堪稱精審,但從考訂引發怎樣的義理,應該是實證類文章同樣應該重視的。清代的章學誠曾經感歎:“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吐絲。”熊十力談研究佛學當由踏實之功而趨淩空之思。文獻的功夫與理論的眼界同時具備,才能提升學術的高度、厚度與精度,偏於其中一隅的學術很可能是跛腳的學術。
4.加強文學論文的文學性。雖然文學研究不等於文學創作,但“文學”論文,講究文字的文學性也是應該的,如果用富於美感的文字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應該是一種更理想的狀態。“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如果我們的論文也能呈現出這麼明媚的學術春景,我相信一定會更有魅力。
參加本屆會議的青年學者很多,這令整個會場充滿了青春的氣息,而且他們提交了不少高品質的文章,這是一種很好的氣象。李白說“丈夫未可輕年少”,這真是一句深邃而有氣度的話。兆鵬會長提議從本次會議開始,在青年學者中設立優秀論文評選制度,這一提議得到了學會領導層的一致同意,這體現了學會對青年學者的關注與提攜之意,我要斷章取義引用劉禹錫的一句詩“好染髭須事後生”來表述這種情懷。我現在特別把這兩句詩合在一起送給到會的青年學者,相信學術史的明天一定更加輝煌。
赞赏